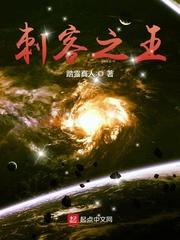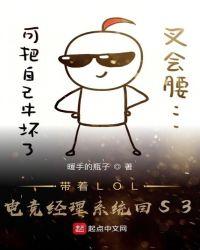笔趣阁>港岛:从九龙城寨收租到大亨 > 第135章 喜事连连求月票(第2页)
第135章 喜事连连求月票(第2页)
“施约翰先生过誉了,您能亲临指导,是黄埔集团的荣幸。”陈耀豪举杯回应,笑容得体,目光却观察著对方殷勤背后的深意。
施约翰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显露出分享秘密的亲昵:“陈生,不知您对『太平绅士”这项荣誉,看法如何?”
“这在香江可是社会地位的象徵,自然知晓一二。”陈耀豪不动声色。
施约翰脸上的笑容更深,带著一种“心腹之人”才有的篤定:“那我要提前道喜了!据可靠渠道的消息,下一季度的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中,陈生您的名字,可是排在最前列!”
他刻意停顿,观察著陈耀豪的反应,仿佛在献上一份精心准备的厚礼。
“以陈生您如今的成就、声望和对香江经济的卓越贡献,这个荣誉,简直是水到渠成。您將成为香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太平绅土,这份荣耀,实至名归!”
他的话语充满了肯定和推崇,姿態放得极低。
“哦?”陈耀豪確实有一丝意外。儘管太平绅士的实权今非昔比,但其象徵意义和社会认可度依然举足轻重。
施约翰此刻主动送上这份“情报”,示好之意昭然若揭。
“多谢施约翰先生提前告知。不过”陈耀豪话锋一转,说道:“我想您今日相约,总不会只为这一桩喜事吧?”
施约翰脸上的热络稍敛,换上一种推心置腹谈正事的表情,但语气依然保持著那份“寻求共识”的亲近,说道:
“陈生果然明察秋毫。实不相瞒,今日前来,一是道贺,二也是想就葵涌港未来的发展,听听你的高见。”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继续说道:“怡和系拿下五號码头开发权的事,陈生想必已经瞭然於胸了?”
这个消息陈耀豪岂能不知?他淡然一笑,甚至带著点“同病相怜”的自嘲:“自然。不瞒您说,我手上也有上好的码头地块,兴致勃勃递了申请,结果嘛——
他耸耸肩,未尽之意不言而喻,“碰了一鼻子灰。”
“唉!”施约翰立刻配合地发出一声深沉的嘆息,脸上写满了“感同身受”的惋惜。
“这简直—令人费解啊!葵涌港如今是什么景象?货轮如织,货柜如山!每日吞吐量早已逼近极限。依我看,別说一个五號码头,就是六號、七號一起上马,也未必能解这燃眉之急!”
他目光灼灼地盯著陈耀豪,带著试探和寻求认同的口吻,“陈生你眼光独到,您觉得——这背后,是不是有些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他將“特殊因素”咬得很重,暗示著华资与英资那微妙的博弈格局。
陈耀豪心中洞若观火,这不过是老生常谈。他端起茶杯,轻啜一口,拋出了一个更具分量的事实:“施约翰先生说得在理。不过,连包船王那样的人物,递上去的码头兴建申请,不也石沉大海了么?”
他巧妙地將包玉刚这面大旗立了起来,
其实哪里是港府断然拒绝?是他和包玉刚这两位只不过是洞悉天机而已,然后,两人心照不宣地主动撤回了申请。
陈耀豪的这份篤定,源於他对未来十年惊涛骇浪的清晰预见。
1973年那场席捲全球的石油危机,如同第一记重锤,將航运业砸入深谷,萧条阴影至今挥之不去,业內普遍预计要到78年才可能喘息。
然而,更大的风暴已在海平线集结一一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滔天巨浪即將接而至,其对全球贸易和航运的室息性打击,將残酷地延续至八十年代中期!
这正是前世记忆中,葵涌后续的六至九號码头,为何要苦苦等到八十年代末才姍姍来迟的根本原因。
在这漫长的十年“冰河期”里,全球货柜货运量將陷入近乎停滯的泥潭。
葵涌港现有的四座码头(还不算怡和即將开发的5號码头),其总运力绰绰有余,甚至可能面临过剩的风险。
陈耀豪那双穿越时空的眼晴,早已看透:此刻耗费巨资去兴建新的深水码头,无异於將真金白银投入一个回报渺茫、甚至可能血本无归的冰窟窿。
他更清楚,未来十年,將是香江船王们集体“渡劫”的悲壮岁月。
无数曾经叱吒风云的航运巨子,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严冬中折戟沉沙,债台高筑。
若非不是他们家底丰厚苦苦支撑,破產清算的噩运几乎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