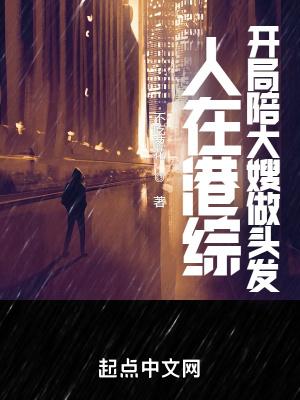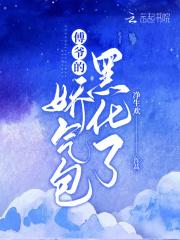笔趣阁>给元白刘柳剧透贬官生活 > 万人行乐一人愁(第5页)
万人行乐一人愁(第5页)
元稹去过嘉会坊的郑国庄穆公主宅第,没有改为佛寺的迹象。他后来根据白居易的《两朱阁》写了新诗,一切也没有变化。
好似之前百炼镜带给他的法力,已经消失了一样。
元稹倒不是失落,只是弹劾奸臣的工具少了一个,仅此而已。淮西的战事,兵败之后,天子李适就此妥协,任他为淮西节度使。
割据一方的身份,彻底落实。
河北回不来,河湟更无望,如今淮西也受不住。
李损之常常为此担忧,但他也不缠着元稹写符咒,毕竟轮到他备考了。
前宰相陆贽,十八岁登科,李损之以他为榜样。
十九岁也行,总之越早越好。
因为他听说今年最年轻的及第者,颇受恩宠。
他可不想向元稹这样在长安蹉跎好几年。
元稹一愣,但李损之转而送他一份之前收集来进士及第者的诗赋。
李损之要认真揣摩。
元稹不愿理会他的暗示。
大唐科举登科率太低,来参加进士科的人有一千多,登科者,今年才十七人。
有人参加过明经科,又去考进士科,参加完博学宏词科,又再考其他制科。直到官职满意为止。
元稹不想浪费精力做这种事。
但是收到诗赋,他拿起来看了看。
今年的赋是《性习相近远赋》,破题简单,这是问《论语》中的“性相近,□□”,但是回答起来,越常见的题,越难以出彩。
今年的诗为《玉水记方流》,有些刁钻。
元稹看李损之在一旁翻书的样子就知道,题目出自《昭明文选》中的某一句。
要是想不起来,就只能望文生义写一首了。
若是背得清清楚楚,那就能答到点子上。
《玉水记方流》出自南朝的颜延之的《赠王太常僧达诗》。这首赠答诗,是夸颜延之的朋友品格高尚,讲的是人才难觅。
王僧达的人生多灾多难,先是怨言谗言相交遭到贬谪,而后升迁为中书令,被人诬陷谋反,死在狱中。
今年进士科录取的人数少,该不会是大多数都答不到点上吧?
这考试的题目真是一年比一年偏门。
元稹听见李损之边上嘟嘟囔囔,问:“你看明白题了,按韵写一下,我拿这些及第者的答卷,比对比对。怎么?不敢?”
“有何不敢?”李损之嘟着嘴,“只是此诗涉及贬官,我觉得晦气。”
“李白还因为谋反入狱呢,你之前还不是天天翻来覆去学着怎么写。”
“南朝的鬼神,和我们大唐不一样。我在书上见过……”李损之点点头,“你不愿意听玄怪的,不跟你费口舌了。”
“不要查《尔雅》。”元稹提醒道,“有朝一日,我要是进了礼部,我就把进士科能带书这件事废掉。”
“那就成了一千人里录一个,不需要制科了。”李损之想了想,“我看他们写得也简单,不查书我也不差。”
那倒是快一点写呀。
元稹见他写了两个字之后就开始斟酌不定。
元稹拿起答卷。
他欣赏不来进士科的诗作。
别人和他的想法一样,甚至有的人中了进士之后,对写诗彻底厌烦。
文辞华丽,内容空洞。
这种诗写久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元稹翻了几页,看到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