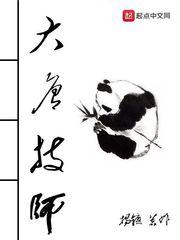笔趣阁>清冷表哥他偏要以下犯上 > 情窦初开(第1页)
情窦初开(第1页)
舒挽回到郡主府时,手脚已是一片冰凉。
她屏退了所有想要上前伺候的丫鬟,独自一人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那辆马车上残留的淡淡药香,仿佛还萦绕在鼻尖,那是宴时身上的味道,也是前世如同噩梦般的死亡气息。
她走到铜盆前,掬起一捧冰冷的水,狠狠地泼在脸上。
刺骨的寒意瞬间钻入毛孔,让她混沌的大脑清醒了几分。
舒挽随手扯过帕子擦干水珠,坐到了案前。
案上摊开着一张宣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和关系网。
她提起笔,在那最顶端的“宴时”二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墨汁洇开,像是一团化不开的污血。
“宴时……”
她低声呢喃,若不是眼中杀意涌动,这声呢喃似情人低语。
那玉芥子果然在他手中。
可要想杀他,谈何容易。
他如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手中不仅握着朝廷的权柄,更掌控着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栖芜宫。
而她呢?
不过是一个借尸还魂的落魄孤女,一个空有头衔,除了美貌一无所有的“清河郡主”。
若宋家纵火案的背后主谋仅是宴时,或许她还能拼上一条命去搏一搏。
可舒挽觉得这主谋绝不仅仅只是宴时。
宋家满门忠烈,究竟是为何要这样对一个镇守边疆的大将赶尽杀绝?
只是因为功高盖主吗?
还是因为那狗皇帝为了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舒挽手中的笔杆被她捏得“咯吱”作响。
若宋家真的是狗皇帝杀的,那她面对的,便是这整个大晋朝的皇权。
蚍蜉撼树,何其可笑。
她颓然地松开手,毛笔滚落在地,染黑了她的裙摆。
不行。
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宴时虽然窃取了她的果实,但他终究不是原来的宫主。
栖芜宫中,那些跟着她出生入死的老部下,真的都甘心臣服于一个弑主的叛徒吗?
只要能收回栖芜宫,她便有了与皇权对抗的资本。
“晏清。”她对着书房外喊了一声。
“姑娘。”晏清闻声进来,单膝跪地,神色恭敬。
舒挽从书桌上取出一叠刚刚写好的信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