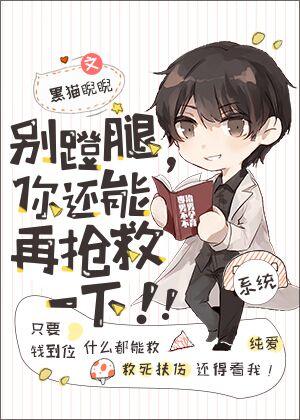笔趣阁>雪城旧事 > 第91章 华北一夜(第2页)
第91章 华北一夜(第2页)
梁秋时这回不在乎有没有得到他的特赦,都朝着他胸口奔过来,滚过来,搂着他的腰,忘乎所以。
将小脑袋埋进他胸口,蹭了又蹭,发丝柔软,划过的时候,直让他心底发痒。
“谢谢你给我配的药,我用过觉着好很多了。”宋郁文说。
甚至这会儿抱着她,愈发熨帖,好像她就是他的药,能为他止痛,免他苦寒。
“我不过雕虫小技,在你那帮御用的军医团里,班门弄斧罢了。是他们不敢给你下虎狼药,每日让你靠一口仙气吊着,又过分迷信中医。我不想让你受苦。”梁秋时其实也怕,怕他缓解了痛处,又伤了其他心肝肺肾脾。
可她舍不得,舍不得看他受折磨。
“我相信你下手有分寸,总归比杜冷丁伤害小很多,也不似鸦片那样坑人。”甚至他在想,若秋时留在自己身边,他这久违的、健康人的舒坦日子,大抵能更长一些。
“其实,我倒宁愿死在你手上。”
这些话,若他从前说,她
哪怕白雪掩埋白骨,也不会在北疆弃他而去。
“我从来不是吃不了苦,不是贪图享乐……”一句话没说完,便又开始带了哽咽。
“我知道,我明白,我都懂。若你受不了一点点罪,怎会陪我过荒原、走沙漠,每天阎王殿里徘徊。”宋郁文将她搂紧,恨不能将她揉碎在骨头里,仔细疼惜着。
“是我没将你照顾好,让你吃了生活的苦,还得吃我的苦,这份苦,便不值得。”
如果光吃生活的苦,他能给一份甜,便怎样的日子都能捱过去。
梁秋时的委屈若潮涌,却没办法融化在久别重逢后、这一夜的温情里。
宋郁文对她有几分无奈,又好笑,语气软软道:“你再哭,把我胸前的衣服都哭湿了一片。”
梁秋时却没他这份好心情,却是问起了:“郁文,我想听听叶记者的事。她为何不在华北?”
宋郁文“哦”了一声,脸上的柔和敛去,却也没有不耐,只说:“她在西北忙工作。”
语气轻松,好似在介绍一个寻常同事。
“可是你受伤了,她在你身边,不是更方便照顾吗?而且,叶记者那么优秀,在华北又不是没有适合她的工作。”梁秋时倒是不再哭哭啼啼,只腮边仍带着泪痕。
“因为她不是我的佣人,可能她觉得,工作比侍候男人更重要吧。我也愿意支持她的工作和理想。”宋郁文说。
对待普通战友,都是理解、鼓励并安慰,何况是
自己妻子。
“可是……”梁秋时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虑:
“我想知道,你同她……有感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