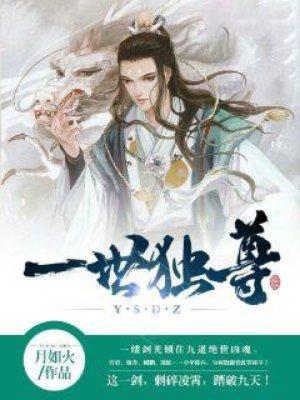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1991:春潮晚来急 > 第59章 哪来的小贱货有娘生没娘养(第2页)
第59章 哪来的小贱货有娘生没娘养(第2页)
“太不专业了,选道具也不知道选个逼真的。”说着,把胡大爷的儿媳妇请过来,“您给看看这是血么。”
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肯定不是血,没有血腥味,浓稠度也不对。”
林芳红和贺远航都心虚地冒出冷汗。
他们本以为,像贺知风这样未出阁的小丫头,是铁定会被这副场景吓到的,结果她不仅不怕,甚至还死盯着不放。
“你,你们是串通好的!”
胡大爷的儿媳妇噌一下站了起来,“放你娘的狗屁!知风是下午临时宴请我们的,她都不知道你会突然出现,怎么提前跟我串通?”
胡大爷一家都纷纷帮腔,指责林芳红陷害不成,胡乱攀咬。
贺知风微微含笑,压低嗓音道:“三婶,用这种阴
损的法子陷害我,就不怕遭报应吗?”
林芳红看到她眼底阴鸷又恐怖的颜色,顿时高声尖叫,挥舞着胳膊要她滚开。
贺知风当即被推了个屁股墩,招娣急得直掉眼泪,拽住时应染的手就往这边拖,“快点,大白兔叔叔,快进去救堂姐。”
时应染便宛如一堵墙,挡在了知风与他们之间。
贺知风仰头看了他一会儿,抓住他的胳膊慢慢站了起来。
林芳红你不是想卖惨么,那就比比看到底谁更惨?
“三婶,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让你这么恨我?几次三番的诬赖、陷害,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算完。以前在我妈跟前说我不孝,我在弟跟前说我争宠,现在又想离间我和三叔的关系,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在京市三年,一直兢兢业业为兴懋斋工作,你却散布谣言,说我做哪种事,可你看看我的手!”
她突然越过时应染,朝林芳红冲了过去。
贺远航眼瞅着想拦,被时应染一个凶狠的眼神钉在了原地。
贺知风一把揪起林芳红的领子,硬生生把她提了起来。
“你倒是说说看,如果我真是干那行的,为什么手会是这样的?”
众人纷纷侧目,瞳孔微缩。
只见贺知风一双手掌心伤痕累累,沟壑纵横,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刀疤,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凹陷,皮肤粗糙得犹如终日干农活的老妇。
林芳红也惊呆了。
“为了给兴懋斋提供雕工精湛的
玉雕、石雕,我天天磨破手指,破了不能包扎,只能拿冰水浸,浸软了又磨,直到表面的皮肤结痂、溃烂,层层脱落露出鲜红的血肉!无数次结痂之后,又把痂子撕开,继续雕。若不这样,我就无法保证雕刻时的手感。若不这样,三叔和二叔就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死命地催!”
“但凡我出不了货,你们就会把我妈搬出来,说我不懂事、有私心,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哪怕我凌晨才刚睡下,也要把我叫醒,根本不管我是不是撑得住。”
贺知风说着缩说着,眼角不由得晕染开一片殷红。
眼泪却始终锁在眼眶中,没有落下一滴。
一只手忽然落在她肩头,让她转过身去。
“别说了,知风,别说了……”时应染心疼快要不会说话,伸手擦过她的眼角,却好像被烫到一般缩回了手。
被她请来吃席的街坊邻里也全都红了眼睛,面带怒容,瞪视着林芳红与贺远航。
“贺老二,还不快把你这毒妇带走!你们贺家长辈如此欺辱小辈,还到处叫嚣知风荒唐,我看你们才是最荒唐的!”
胡大爷气得把拐杖砸在地上,咚咚作响。
很快,这两人被大家伙齐心协力轰出了郑家茶馆。
如此同仇敌忾的一幕,简直是周县难得一见的奇景。
站在三楼的郑老二则脸色阴沉地抠破了木头栏杆,方才他一直低头默默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一切,要不是知风有言在
先,不准他出手,他早把林芳红和贺远航扔进江里去了!
不过贺知风这么做,确实是解气。
贺远航不是最好面子么,那就索性让他面子、里子丢个精光,好好品尝一下被人唾弃、藐视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