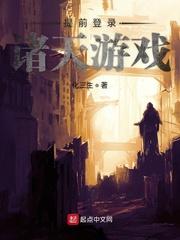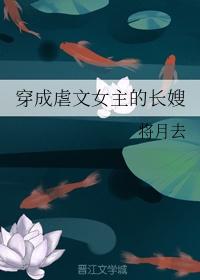笔趣阁>外科教父 > 1234章 生存功利(第3页)
1234章 生存功利(第3页)
“怎么,怕?”李泽会挑眉。
“不怕,就是……太突然了。”
“外科医生的成长没有循序渐进,只有实战。”李泽会拍拍他肩,“记住,站上手术台,就要忘记恐惧,眼里只有病灶和生命。”
当晚,夏书失眠了。他反复回忆导师教过的每一个步骤,查阅最新指南,模拟器械传递顺序。蔡巧君陪在他身边,轻声说:“你已经准备得很好了,相信自己。”
次日七点半,他提前到达手术室。消毒、铺巾、穿手术衣,动作沉稳。八点整,李泽会准时入场。
麻醉已完成,患者是一名五十二岁女性,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左心房显著增大。李泽会戴上放大镜,拿起刀片,淡淡地说:“切皮。”
夏书屏住呼吸,接过电刀,沿着胸骨正中线缓缓推进。血液渗出,迅速被吸引器清除。电锯响起,胸骨被整齐劈开。打开心包,跳动的心脏暴露在视野中。
“很漂亮的心脏。”李泽会说,“结构清晰,没有严重粘连。这是我们的幸运。”
体外循环开启,心脏停跳。李泽会手持剪刀,精准剪除病变瓣膜,测量瓣环直径,选择合适的人工瓣植入。每一个缝合针距控制在两毫米以内,手法如绣花般精细。
“注意打结力度,”他提醒夏书,“太紧会撕裂组织,太松会漏水。”
夏书协助持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缝合技术??稳定、流畅、毫无多余动作。
手术历时四个小时,顺利完成。关胸时,李泽会突然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能放弃美国的一切回来吗?”
夏书摇头。
“因为我父亲临终前对我说:‘你在美国再成功,也只是个外国医生。回去吧,给中国人做几台救命的手术,才算真正活过。’”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我不想等到老了才后悔。”
手术室陷入沉默。只有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
术后第七天,患者顺利拔管,转入普通病房。复查超声显示人工瓣功能良好,无反流,心功能明显改善。
李泽会站在床边,看着老太太握着孙子的手笑出眼泪,转身对夏书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那一刻,夏书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外科教父”。
不是技艺多高超,不是名声多显赫,而是心中始终装着病人,哪怕跨越半个地球,也要回来点亮一盏灯。
心脏外科的第一台手术成功了。但这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泽会带领团队连续完成五台高难度手术:主动脉夹层孙氏手术、先天性心脏病法洛四联症根治、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每一台都堪称教科书级别。
媒体争相报道,“三博医院迎来心脏外科新时代”成为热搜话题。患者慕名而来,预约名单排到了三个月后。
而最让杨平欣慰的是,夏书的成长肉眼可见。他不再只是被动执行指令,而是开始独立思考,提出优化方案。有一次术中突发大出血,他果断调整灌注策略,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李泽会在晨会上公开表扬:“夏书,你有成为一名优秀心脏外科医生的潜质。继续保持。”
这句话,比任何奖金都珍贵。
某夜,杨平站在住院楼顶层天台,望着灯火通明的心脏外科病房,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李泽会发来的微信:“我已经递交了中国绿卡申请。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
杨平笑了。他抬头望向星空,喃喃自语:“韩主任,您看到了吗?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