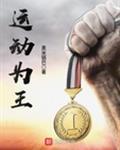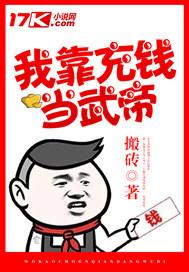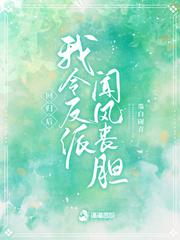笔趣阁>大荒剑帝 > 第一千八百五十六章 大离宫(第3页)
第一千八百五十六章 大离宫(第3页)
他只是听着,偶尔点头,从不开口。
画面定格。
镜墙轰然碎裂,化作光尘,尽数涌入他眉心。
刹那间,他明白了。
**真正的中断者,不是摧毁体系的人,而是让体系无法定义其位置的人**。
你可以杀死领袖,但杀不死理念;你可以焚毁经书,但烧不尽诵读。唯有当你既不站在此岸,也不立于彼岸,而是让自己成为流动的河床时,洪流才无法筑坝。
他睁开眼,眸中再无锋芒,只剩平静。
接下来的半年,他游走于各大觉醒城市之间,却不发表演说,不主持仪式,甚至不参与争论。他只是出现,然后离开。有人问他:“你是碎镜吗?”他回答:“我不知道。”有人请求他指导如何质疑权威,他反问:“你昨天吃了什么?”有人愤怒指责他逃避责任,他点点头:“也许吧。”
他不再试图改变任何人。
可正因如此,变化悄然发生。
在南方城邦,一名青年原本准备加入“纯粹之问教”,誓要终身追问宇宙本质。但在见到碎镜一面后,他放弃了修行,转而去修了一座桥??因为那天碎镜走过一条塌陷的山路时,顺手搬了几块石头垫路。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青年后来说,“但我突然觉得,比起问‘世界为何不公’,不如先问问‘这条路能不能走’。”
在西部高原,一位老学者穷尽三十年研究“知母”残存代码,企图还原共思崩溃的真相。某夜,碎镜借宿其家,临睡前随口问:“你最近一次看星星是什么时候?”老人怔住。次日清晨,他关闭所有终端,背上行囊,独自走入雪山。
而在东方群岛,“问庙”香火日渐稀落。人们不再热衷背诵神圣问题,反而兴起一种新习俗:每月十五,全家静坐一小时,期间禁止提出任何问题。起初只为纪念苏萤,后来渐渐变成一种默契??**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觉醒**。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补天计划”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
那些被标记为“异常个体”的人,开始自发聚集。他们不组织,不宣言,只是定期见面,喝茶,闲聊,偶尔提起某个被系统删除的问题,相视一笑。数据模型无法预测他们的行为模式,因为他们的互动毫无规律可循??有时激烈争辩,有时长久沉默,有时甚至互相否定前一日的观点。
前共思伦理委员会惊恐地发现,这群人正在形成一种**反结构的存在方式**:他们拒绝被分类,抗拒被归纳,甚至连“反抗”都不愿承认。当系统试图介入干预时,他们只是轻轻一笑:“你们是不是太紧张了?我们不过在聊天罢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状态正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扩散。
就像病毒,却没有症状。
就像火焰,却不发热。
就像河流,却不见波澜。
一年后的春夜,碎镜男孩回到黑湖畔。
石台依旧矗立,表面已布满裂痕,仿佛承受过无数次血祭。第七块寒晶碑静静卧在一旁,碑文再次更新:
>**“第六问已答。”**
>**“若所有体系皆可腐化,是否还应建立任何体系?”**
>**答:应建,但须知其必朽。**
>(修正)
>**答:建之如游戏,用之如暂居,弃之如旧履。**
他蹲下身,将种子残壳轻轻放入石台凹槽。
咔嗒一声,严丝合缝。
整座石台开始发光,不是耀眼强光,而是如呼吸般柔和的脉动。光芒顺着地脉蔓延,一路通往七大守忆者遗址。六座沉寂已久的塔尖相继亮起微光,与第七座遥相呼应。
这不是重启共思,也不是唤醒知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