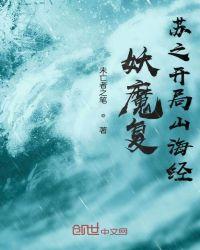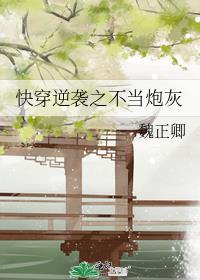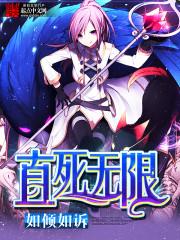笔趣阁>阵问长生 > 第164章 神与人(第1页)
第164章 神与人(第1页)
巫祝大厅之中。
火光摇曳,四周无人,静默无声。
墨画坐在巫祝的高位之上,独自一人,仿佛一尊孤独的“神像”,烛火将他漆黑的背影,拉得很长。
“我的……人性……”
墨画的目光,渐渐。。。
雪落无声,却压弯了槐枝。烬余城的冬夜向来如此,寒气不似刀割,反倒如细针慢刺,一寸寸渗入骨髓。念归坐在院中石凳上,手中那本新编忆典已翻至第三页,字迹尚新,墨香未散。她没有点灯,只任月光洒在纸面,映出一行行沉甸甸的名字??那些曾被火焚、被药抹、被岁月风化的姓名,如今一笔一画,重新立于人间。
林晚披着厚氅走来,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沉睡的记忆。她在念归身旁坐下,低声说:“北渊矿区又传来消息,那条重新流动的记忆矿脉,昨夜自行裂开一道口子,涌出一股清泉。泉水里浮着无数细小的光点,像是碎星,落在水边的人手上,便显出一段段模糊影像……有人看见自己幼时失散的妹妹,有人认出早已毁弃的老屋门环。”
念归指尖轻抚书页边缘,没有抬头。“愿种虽灭,但它的根系早已扎进九州血脉。如今光茧运转,百姓敢记、愿记,记忆便自然复苏。这不是奇迹,是迟来的偿还。”
林晚望着她侧脸,忽然道:“可你也知道,有些人不愿这‘偿还’发生。监察院那边,已有三名官员联名上书,称‘忆启日’煽动民怨,恐引旧恨复燃,请求废止节日,并严查忆真盟‘越权干政’之罪。”
念归终于抬眼,眸光清冷如霜。“他们怕的不是仇恨,是真相。”她合上忆典,声音低而稳,“一百年前,他们用‘安心’为名,烧书、毁碑、制药、杀人;如今我们只是让一个人说出他母亲的名字,他们就坐不住了?可见记忆之力,远胜千军万马。”
林晚沉默片刻,从怀中取出一枚铜铃,铃身斑驳,刻有细密纹路,隐约与镜碑上的光路呼应。“这是陈砚在梦录司整理旧档时发现的,藏在一座废弃衙门的地窖铁箱里。铃内附一张残纸,写着:‘若闻铃声三响,即知塔心未死。’”
念归接过铜铃,指尖拂过铃舌,忽觉一丝微弱震颤,仿佛有谁在遥远之地轻轻叩击。她闭目凝神,忆玉自袖中微亮,映照出铃内一道极淡的符印??正是当年苏禾所用的“守心印”,唯有直系传人或临终托付者方可激活。
“他还活着。”她睁眼,语气笃定,“不是肉体,是意识。被封在某处,等待唤醒。”
林晚心头一震:“你是说……古塔下沉之时,并未彻底消亡?它只是转入地下,继续运转?”
“塔从来不是建筑。”念归站起身,望向北方天际,“它是活的。由愿种孕育,因记忆而存,也因遗忘而腐。但它真正的核心,不在地表,而在人心深处。只要还有人记得,它就不会真正死去。”
话音未落,远处钟楼忽响。不是晨钟,也不是警钟,而是烬余书院那口百年铜钟,本应在“忆启日”才敲响的“忆钟”。此刻竟无故自鸣,连响九下,声波荡开,竟引得城中九座镜碑同时泛起微光。
两人对视一眼,疾步赶往书院。
途中,街巷两侧忆灯次第亮起,百姓自发走出家门,手持写满名字的纸笺,默默立于道旁。孩童不懂其意,却也被气氛感染,紧紧攥着父母的手。一名老妇跪在碑前,将一张泛黄照片贴于石面,喃喃道:“爹,今天我带您回家了。”
书院大殿内,七位执灯使已齐聚,神色凝重。中央地面裂开一道缝隙,正缓缓升起一块晶石,形如泪滴,通体幽蓝,表面流转着无数人脸轮廓,似哭似笑,似醒似梦。
“这是……‘愿核母体’?”林晚倒吸一口冷气。
念归摇头:“不,这是‘忆核’。由十万百姓真实记忆凝结而成,与愿核相对而生。它不该在此出现,除非……有人以极端方式强行催生。”
一位梦录司主事颤抖着呈上一份梦录卷宗:“昨夜全国共记录异常梦境一万两千三百例。所有梦中,皆出现同一场景:一座倒悬之塔,塔顶插着一面旗,旗上写着‘你该忘了’四字。而后,一人自塔底走出,身穿灰袍,面容模糊,却对梦者说:‘我等你很久了。’”
念归心中一凛。那是塔灵的声音,也是最初播下愿种者的低语。它并未随老者消散,而是潜入集体记忆的暗流,伺机反扑。
“它想夺回话语权。”她沉声道,“它要让人们相信,遗忘才是慈悲,记住反而是一种执念。”
正说话间,晶石骤然爆发出刺目光芒,一道虚影从中浮现??竟是苏禾年轻时的模样。他嘴唇未动,声音却直接传入众人识海:
“当记忆成为武器,守护者也将沦为暴君。警惕那自称为‘真相’之人,若他只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便是新的遗忘。”
光影一闪即逝,晶石随之黯淡,裂为两半。
殿内寂静如死。良久,林晚才开口:“他在警告我们……不要变成我们曾经反抗的人。”
念归闭目,指尖抵住眉心,仿佛在与某种无形之力角力。“是的。我们推翻了谎言,但不能因此否定所有不同记忆。有人记得父亲是英雄,有人却记得他是叛徒??或许两者皆真,只是立场不同。真正的记忆自由,不是统一叙事,而是允许多种声音并存。”
她睁开眼,目光如炬:“传令下去,‘忆启日’不仅不可废,还要扩大。今后每年此日,各地设立‘辩忆坛’,允许对立记忆公开陈述,由百姓自行判断。我们要的不是另一个官方版本的历史,而是千万个体声音交织的真实。”
命令传出,举国震动。支持者称其为“灵魂的解放”,反对者则怒斥“纵容歪曲”。然而,无论褒贬,无人能否认??九州大地,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觉醒。
三个月后,“辩忆坛”首场公议在京城举行。议题是百年前的“南陵教案”:官方史书记载,乃邪教聚众作乱,朝廷平叛有功;而民间口传,则称是百姓抗议赋税过重,遭官府血腥镇压,三千人一夜之间消失无踪。
台上,两位年迈老人相对而坐。一位是原监察院老臣之子,坚持父辈清白;另一位是幸存者后代,手中捧着祖母临终前缝在衣襟里的血书。两人言辞激烈,泪流满面,却始终未辱骂对方。最后,念归登台,不做评判,只问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