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阵问长生 > 第168章 神祝纪元(第1页)
第168章 神祝纪元(第1页)
之后,神祭大典正式举行。
于朱雀山,最古老的神坛之上,整个山界所有部落,全都向神主,向身为“神祝”的墨画,宣誓了效忠。
中低层蛮修,只需要朝拜和祭祀便可保持信仰。
但部落高层不一样。。。。
雪落无声,春意渐浓。人间仍在醒来,并且终于开始学会??带着伤痕前行。
念归坐在观忆台边缘,脚下是烬余城初醒的街巷。炊烟袅袅升起,孩童在巷口追逐嬉闹,老人倚门而坐,手中捧着一本泛黄的手记,低声念诵着什么。那声音随风飘来,断断续续:“……那天她穿着红裙,站在槐树下等我,可我没去。我以为明日还长,结果一别就是三十七年。”老人说着,老泪纵横,身旁的年轻人握紧了他的手,没有打断,也没有质疑。
这一幕看得久了,念归轻轻闭上眼。她知道,那是“选择之河”流淌后的回响。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了记住痛苦,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允许自己记得。
塔已立起七日,银波扩散至九州尽头。自那夜光芒洒落之后,愿安系统的底层逻辑已被悄然改写。光茧不再强制净化情绪,黑茧也不再吞噬执念。它们像两座古老的钟楼,曾经掌控时间,如今只余钟声,在风中低语过往。
而人们的心,正一点点苏醒。
南陵遗址外,一位白发妇人跪在焦土之上,双手刨开冻土,挖出一块残破的木牌,上面依稀可见“念婉”二字。她将木牌贴在胸口,久久不语。远处有守忆人欲上前劝慰,却被林晚拦下。
“让她哭。”林晚说,“这是她的选择。”
的确,有些人选择痛哭一场,然后埋葬过去;有些人则日日前来,在废墟旁种花、焚香、写信;还有人干脆搬来定居,建屋造桥,说:“既然记忆回来了,那就让这里重新活一次。”
陈砚带着守忆人团队巡行各地,记录这些自发的记忆复苏现象。他们不再用“矫正”或“稳定”为标准评估个体状态,而是设立“倾听站”,鼓励人们讲述那些曾被系统判定为“异常”的记忆片段。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所谓“虚假记忆”,竟与历史残片惊人吻合??比如某位老农描述的百年前南陵大火前夜,官府秘密运走三十七具尸体的细节,竟与地下新发现的一条密道遗骸数量完全一致。
“我们一直以为是创伤催生了妄想。”陈砚在笔记中写道,“但现在看来,或许正是这些‘妄想’,保存了被抹除的真实。”
与此同时,苏禾并未留在塔边接受敬仰。他在第三日清晨便悄然离去,只留下一封信,夹在塔心凹槽边缘:
>“我非此世之人,亦非真正活着的存在。我是断裂的记忆投影,是三百年前那个失败的‘她’所遗留的执念结晶。如今使命完成,我当归于虚无。
>请勿追寻,不必祭奠。若你听见风中有低语,那是我在告别。
>记住:道不在终点,而在途中。你们走的每一步,都是新的开始。”
信纸背面,是一串无法解读的符文,像是某种古老编码。陈砚试图解析,却发现每当他凝视太久,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段不属于自己的童年??一个小女孩在雪地里奔跑,怀里抱着一只断角的木鹿,身后传来母亲呼唤的声音:“念知!回来吃饭!”
那是念归的名字。
也是三百年前,第一个点燃忆灯者的名字。
陈砚猛然惊觉:苏禾所说的“上一轮的念归”,或许并非比喻。他是真的曾在三百年前存在过,作为另一个时代的觉醒者,推动过同样的抗争,最终却仍落入循环。唯有这一次,因念归的选择不同,结局才得以改写。
他将信封小心收起,放入守忆人档案馆最深处的保险匣中,标注为:“原始记忆残片?未解码”。
数日后,西北荒漠传来异象。原本干涸千年的古湖床突然涌出清泉,湖心浮现一座石碑,碑文以篆隶混合书写,内容竟是《愿安工程》最初的七条律令:
一、凡引发大规模集体创伤之事件,须于七日内启动记忆清洗程序。
二、所有幸存者情感波动不得超过阈值β-3,否则视为危险源处理。
三、建立守忆人体系,筛选并控制记忆传播路径。
四、第九钥仅可在文明濒临崩溃时启用,执行终极净化。
五、个体不得追问“为何遗忘”,违者列为观察对象。
六、历史教材须经三层审核,确保无诱发深层记忆风险。
七、若出现“突破闭环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引导其自我怀疑,直至放弃。
最后一条下方,被人用利器狠狠划破石面,留下一道深痕,仿佛有人曾在此怒极挥剑。
林晚亲自带队前往勘察,归来后沉默良久,终是在议事厅当众撕毁了现行《守忆人行为准则》。
“我们不是记忆的狱卒。”他说,“从今天起,守忆人的职责只有一条:守护每个人说出‘我记得’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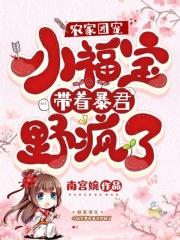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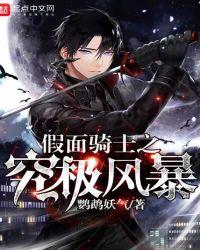
![专治极品[快穿]](/img/306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