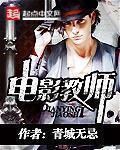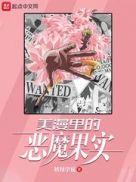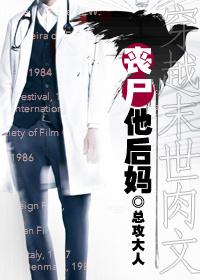笔趣阁>文豪1983 > 第55章 绝不原谅(第3页)
第55章 绝不原谅(第3页)
林晚双手接过,郑重鞠躬。老妇人笑了,用生硬的汉语说了三个字:“谢谢……听。”
返京途中,飞机穿越云层,舷窗外阳光刺眼。林晚靠着窗睡着了,手里仍紧紧抱着那把琴。我打开笔记本,写下此行总结:
>“在阿咩朵村,我终于理解了‘语言之外的语言’。
>当文字无法承载痛苦,当科技显得冰冷,歌声成了最原始也最坚韧的沟通方式。
>它不追求清晰逻辑,也不在乎音准节奏,只为证明一件事:
>我存在,我感受,我需要被听见。
>
>‘民谣归还计划’正式启动。
>目标:五年内覆盖全国五十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建立一百个‘声音驿站’,培训一千名本土声音守护者,
>归档一万段濒临消失的民间心声。
>
>我们不做抢救,只做陪伴;
>不做展览,只做传承。
>让每个普通人相信??
>即使无人鼓掌,你也值得发声。”
回到北京已是深夜。办公室灯还亮着,助理留了张纸条:“周哲远来电三次,说沈云卿家属想见您。”
第二天上午,我在出版社楼下见到了沈云卿的儿子沈磊。他比照片上年迈许多,鬓角斑白,眼神却依旧锐利。
“我母亲临终前最后说的话,是通过你们发布的吧?”他开门见山。
我点头:“是的。那段黑胶唱片里,她说了‘儿子,妈妈不是不想抱你,是怕自己不够格’。”
他沉默良久,从包里取出一只牛皮信封:“这是我父亲三十年前写给她的信,从未寄出。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在床头柜暗格里找到。”
我接过信,小心翼翼展开。字迹潦草,情绪激烈:
>“秀兰:
>二十年了,我还是叫你秀兰,因为那是我唯一敢直呼的名字。
>我知道你嫁给别人了,过得清贫但安稳。而我,在文学圈虚名浮利中打滚半生,回头一看,竟无一人可交心。
>那年你拒绝我的求婚,说‘我们之间隔着太多时代的眼泪’,如今我才真正明白。
>如果重来一次,我不再追求什么大师称号,只想做个能听懂你沉默的人。
>可惜,太迟了。
>
>儿子问我:‘爸爸为什么总听那盘磁带?’
>我说:‘那是妈妈的声音,也是我这辈子错过的一切。’
>
>秀兰,若你还活着,请替我听一听这个世界。
>若你已离去,请让我在录音里,再说一遍:
>对不起,我爱你。”
信纸末端附着一行小字:“请将此信录入‘万家录音’,编号【00000】,标题为《迟到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