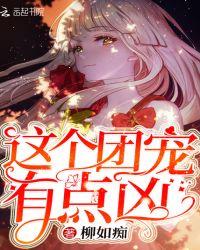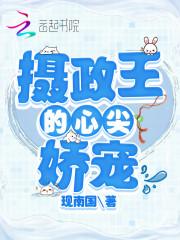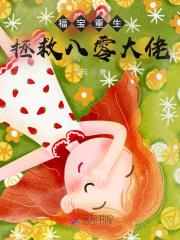笔趣阁>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3章 是的他是陈瑾(第1页)
第493章 是的他是陈瑾(第1页)
2013年1月20日,陈瑾《达拉斯》的最后一场戏。
还未开拍,但所有人却都在站在了化妆室前,等待着陈瑾的走出,包括朱颜曼兹、宝拉还有王媛媛;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今天杀青,给他的特别见面礼亦或者惊喜。。。。
林默醒来时,窗外的阳光已经铺满了半间屋子。他没开灯,就那样坐在床沿,盯着地板上那道从窗帘缝隙斜切进来的光束,像一条通往过去的路。昨晚写下的文字还在电脑屏幕上亮着,光标在句尾一闪一闪,仿佛在等他说完未尽的话。
他起身泡了杯浓茶,走到工作室。老放映机还立在原地,胶片已收好,但镜头微微发烫,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放映。他伸手摸了摸机身,指尖触到一丝温热,忽然笑了??这机器,竟比人还懂得记得温度。
手机震动起来。是陈屿发来的消息:“《底片人生》第一章我看了,凌晨三点哭得像个傻子。你什么时候出书?我要第一个买。”
林默回:“还没写完,连大纲都乱七八糟。”
“那不重要。”陈屿很快回复,“重要的是你说真话了。现在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合格’?你把耻辱变成了勋章,这才是真正的表演课。”
林默盯着屏幕许久,最终只回了一个字:“谢。”
他知道陈屿说得对。过去他总怕提起艺考失败的事,怕被人说“混了二十年还是个无名之辈”。可当他真正写下那段经历时,才发现那些羞于启齿的日子,早已成了他最坚硬的骨骼。
下午,养老院打来电话,说张桂兰想见他。
林默赶到时,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她抬头看见他,眼睛一亮:“你来了,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
林默蹲下身:“妈,您别着凉,进屋说吧。”
“不急。”她摇摇头,把照片递过来,“你看这个。”
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站在文化馆门口,背景是八十年代特有的红砖墙和水泥标语牌。他们穿着朴素,有人抱着录音机,有人提着摄像机,脸上却洋溢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林默一眼就在角落里认出了母亲??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这是……你们剧团?”
“不是剧团,是我们自发组织的‘民间影像记录小组’。”张桂兰声音轻缓,像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梦,“那时候没人支持我们拍普通人,说是‘没有价值’。但我们不管,谁家办喜事、谁家老人过世、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我们都去拍。我们相信,历史不该只有伟人的名字,也该有普通人的呼吸。”
林默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边缘:“那后来呢?”
“后来啊……”她叹了口气,“政策变了,经费断了,设备被收走,人也散了。有人说我们疯了,说我们浪费青春。可我不后悔。你记得你小时候问我,为什么非要用那么旧的机器放电影吗?”
林默点头。
“因为胶片是有体温的。”她说,“数字可以复制,但那一格一格亲手穿过镜头的画面,是活的。它记得按下快门的人心跳多快,记得取景框里那个陌生人眼里的光。”
林默喉咙一紧。
“你现在的课,其实就是在延续这个。”张桂兰握住他的手,“你以为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不,是你从小看着我做的事,在你心里埋了种子。只是你一直没意识到罢了。”
林默低下头,眼眶发热。
“所以别怕走得慢。”她轻声说,“跑龙套怎么了?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记下了那么多眼神、那么多沉默、那么多欲言又止的瞬间。这些,才是真正的剧本。”
那天晚上,林默翻出了母亲当年的工作笔记。厚厚三本,纸页发脆,字迹工整。他在其中一本的扉页上看到一行小字:
>“致未来的放映员:当你打开这本笔记时,请记住,每一个愿意被镜头注视的人,都值得被世界温柔以待。”
他合上本子,拨通了小舟的电话。
“明天能来一趟工作室吗?”他说,“我想重启一个项目??叫《普通人档案》。用最原始的方式,拍真实的故事,不剪辑、不美化、不设结局。就像我妈当年做的那样。”
小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哥,我能带我爸一起来吗?他最近说话多了些,昨天居然问我,‘咱们还能再去演一次吗?’”
林默笑了:“当然能。而且这次,我们要让他当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