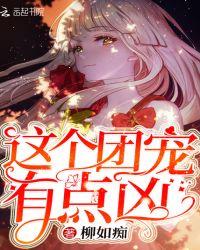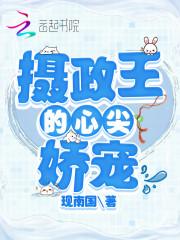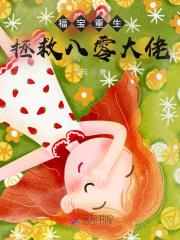笔趣阁>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3章 是的他是陈瑾(第2页)
第493章 是的他是陈瑾(第2页)
第二天清晨,六点不到,工作室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小舟推着父亲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学员??一个是曾在殡仪馆工作过的女孩阿阮,另一个是曾做过夜班护工的男生大川。他们都带来了想记录的人:阿阮的母亲,一位独居多年的老裁缝;大川的师傅,一个在医院值了一辈子夜班的清洁工。
林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台老式手持摄像机??是他托人从各地淘来的二手货,有些甚至还能用磁带录制。
“今天我们不讲课。”他说,“我们只做一件事:陪着你想拍的人,走一段他们的日常。记住,不要引导,不要打断,更不要试图‘升华’。你就站在那儿,像个影子,让他们忘记镜头的存在。”
第一组去了菜市场。阿阮陪着母亲去买布料。老人动作迟缓,在一堆花布前犹豫良久,最后选了一块淡蓝色的棉麻。“这是我给你爸做结婚衬衫用的那种。”她低声说,手指轻轻摩挲着布面,“他还穿着那件睡衣,躺在柜子里,没舍得扔。”
阿阮没说话,只是静静地拍着。镜头里,阳光透过棚顶的塑料布洒下来,照在母亲斑白的鬓角上,像一层薄霜。
第二组去了医院地下室。大川带着师傅巡视夜间通道。老人佝偻着背,一手提灯,一手扶墙,每走到一处拐角,都会停下来擦拭消防栓上的灰尘。“这不是任务。”他说,“这是尊重。这些人白天治病,晚上睡觉,不能让他们醒来看见脏兮兮的走廊。”
大川跟在他身后,镜头微微晃动。他忽然问:“师傅,您干这行三十年,有没有人跟您说过谢谢?”
老人笑了笑:“有啊,一个小孩,发烧住院,半夜迷糊着喊‘爷爷开灯’。我开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不怕了’。那一刻,比什么奖金都值。”
第三组留在工作室。小舟让父亲坐在椅子上,放了一段他们上次演出的录像。起初老人没什么反应,直到画面里出现他自己颤巍巍说出“女儿”两个字的那一幕。
他突然抬手,指着屏幕,嘴唇微动:“这……是我写的?”
小舟含着泪点头:“是您写的,爸。”
老人怔怔地看着,忽然伸手去摸纸上的指纹印,嘴里喃喃:“小舟……小舟……”
那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完整叫出她的名字。
林默站在一旁,没有靠近,也没有说话。他只是按下录制键,让这一刻静静流淌进胶片的脉络里。
傍晚收工时,所有人都疲惫却明亮。他们在院子里围坐一圈,分享今天拍到的画面。没有点评,没有打分,只有倾听。
轮到阿阮时,她播放了母亲回家后的一幕:老人坐在缝纫机前,拿起那块蓝布,开始裁剪。镜头缓缓推进,只见她一边缝,一边哼起一支几十年前的老歌。歌声很轻,几乎听不清词,但那种温柔,却穿透了所有技术缺陷。
“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她还爱着他。”阿阮说,“但她用了整整一夜,缝了一件男式衬衫。她说,‘不知道他还穿不穿得下,但万一哪天他回来呢?’”
没人说话。风吹过树梢,梧桐叶沙沙作响,像在替所有人鼓掌。
林默轻声问:“你们觉得,什么是真实的表演?”
大川想了想:“是不是……当你不再想着‘我要感动谁’,而是‘我只是想留下他’的时候?”
林默点头:“对。表演的本质不是征服观众,而是忠于所爱。”
几天后,《普通人档案》的第一批样片完成。林默将它们剪成一部三十分钟的合集,命名为《光隙》??意为在生活的裂缝中,总有光透进来。
他把片子上传到一个独立影像平台,附言只有一句:“献给所有被忽略的时刻。”
没想到,短短三天,播放量突破百万。评论区涌来无数留言:
“我奶奶也这样,每天给我爸叠军装,尽管他已经牺牲二十年了。”
“我在ICU外录下了妈妈最后一句‘宝贝晚安’,现在每次难过就听一遍。”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偷偷爱着回忆。”
更有媒体联系采访,问林默是否考虑商业化运作,比如推出系列纪录片、开设付费课程。
他一一婉拒。
“这不是生意。”他对记者说,“这是还债。我还给我母亲,还给那些年我在片场看见却无力记录的脸,还给所有以为自己不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