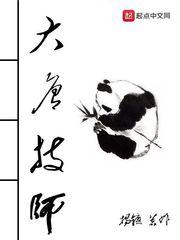笔趣阁>贞心淫骨绿意简 > 第52章(第7页)
第52章(第7页)
我耐心等待着,终听到他长叹一声:“她夫婿是个怯弱老实人,是陈家从外面捡回来的孤儿,和陈卓姐一块长大,两人情同兄妹,非常相爱,陈阿爹为他俩直接操办了新婚嘉禧,偏生我未婚妻、岳家和家父都信这个……唉!”
我听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隐隐猜到什么,便没再多问。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夏管事推开雕花门扉,朝我比了个手势:“贵客请进。”
我进到大厅之后,看见老地主正凑近那宋公头部,跟他低声交流着什么,表情晦暗不明,两人的眼神不时地看向我。
老地主似乎和他达成一致,蹒跚着走过来,告诉我结果:“宋公提出:命可留,根须断。他还有一个条件——”
然后他将我拽到一处角落,压低声音向我耳语:“他要授你一道往生渡魂咒,你以后行房之时须默念此咒,助他惨死的儿子早入轮回!你快答应宋公吧,他心事已了,能不能回到家都不好说,已在弥留之际了。”
看着躺椅上那具形销骨立的高大身躯,我觉得这执念既荒诞又令人心酸,感念这个大豪侠的慈悲心怀和不幸遭遇,便同意了这个请求。
宋公如同一具披着人皮的高大骷髅,见我靠近,浑浊的眼珠微微转动,干裂的嘴唇轻颤。
我俯下身,听他气若游丝地向我传授那段咒诀:“你将来行房之前须默念我儿姓名宋东璟三声,之后念这段咒语:咤唎嘛咪吽唵呢,……行房之前还需运转真炁,以意引炁,自丹田起,沿任脉下行至会阴,转而逆闯尾闾关,分三路盘旋而上,以内力护送阳精至紫宫!”
此时,周围人等在老地主的示意下,均后退数步,老地主自己也避得远远的。
然后宋公还让我立下重誓,非良善之人不得传授。
他儿子竟要借我将来妻室的肚子转世,成为我的儿子!一股难以名状的荒诞感顿时涌上心头。
而且这样的法术谁会修习?亡魂是否重入轮回,又有天知道!
但我还是依言立下了这古怪的重誓,决不轻易传于外人。这次的闽西之行,我遭遇的怪事可说一桩接一桩。
老人见我郑重应下,眼中露出欣喜的目光,随着喉间一声似哭似笑的呜咽,重重点了点头。
“留人不留根”看似残忍,实则是在这民风彪悍的闽西之地,给令家幼子留了活路。
想想那些被害的苦主,哪个不是跺跺脚就能让州县震动的地方豪族?
若非这般处置,那孩子早晚要被人报复凌虐而死。
老地主像一头愤怒的野猪一样转着圈,到底心有不甘,拽着我的胳膊拖到角落,眼中闪着野兽般的凶光:“令阳奇的娘子,我明天便会接过来,以后便做我的十一娘。等她与我燕侣双俦,再也离不开我之后,我会亲手熬一盅肉羹给她吃——”
他龇着金牙狞笑,“再告诉她,那是用她儿子的命根子做的。”
我一听此话,只觉一阵恶心,强压下翻涌的胃液,拧着眉毛质问他:“你为人何至于此?你会逼疯她的!”
老地主仰天大笑,“我跟着大哥行善七年,便收到了这个恶果!我最心爱的女儿,我最爱的妻子,……”他猛地指向天空,“这贼老天!非要我熬化做成一只臭夜壶,那我便继续做恶人吧!”
他所经历的炼狱般的心灵苦楚让我心生怜悯,但这厮沉迷于这些悖逆人伦之事,也让我非常厌恶,不禁痛斥他道:“那林姓矿工虽死于矿难,你就没有几份责任?反而与未亡人媾和,一而再、再而三,行这等猪狗不如之事!我还是劝你读读佛经!”
他眼中闪过一丝讥诮:“人死如灯灭,亲人、家业统统抛开!一副枯骨,如何在意我与他妻子媾和?我不过是扮一幅恶相吓唬活着的矿工。说到尊重,生者对亡者最残忍的亵渎,从来不是改嫁偷欢,而是遗忘!”
没想到他竟是如此彻底的格物……一时间我竟无法反驳他的话。
“你以为佛经是万灵药?全是虚无缥缈的废话,像你这等没有慧根之人,纵使诵经万遍,也不过是唇舌相磨,如石上泼水,半点不沾心!你一个小小毛孩子,莫要轻易与人说佛,到处显摆!”
我胀红了脸,冷笑一声:“菩萨若有势力堪任,应治恶人治而不嗔。这样的智慧,你也敢轻视吗?小心报应!”
他厉声诘问:“令阳奇害了这么多无辜夫妻,你为何不与我谈现世报应?为何不能报应在他亲眷身上?”
我毫不留情地反驳:“令阳奇造业时,可曾让亲眷同持刀?可曾与妻儿共谋算?佛说自作自受,正谓业力如影随形,却只追那形骸本身。你这般急着要报应他的亲眷,不过是为内心之恶找一个宣泄口!”
“内心之恶?哈!你以为善恶对立?大谬!恶才是公义的利刃,是文明的铁盾,是秩序最忠实的扈从!善意常常需要理由,恶意却可以毫无缘由,你想过原因吗?”
然后他开始发表一通善与恶的谬论:“人在一念之间,涌现的全是恶意。空谈道德的年代,人心最是败坏!明面上都有道德洁癖,暗地里皆是男盗女娼。我宁愿恶得坦荡,也恶得理直气壮!”
我再没兴趣听他扯鬼话,此时倒突然觉得“菩萨若有势力堪任”这句话极有深义——本来只是想与他说“治而不嗔”才带出来的——见地,修持,行愿,这竟是工业化菩提道次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