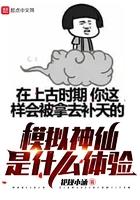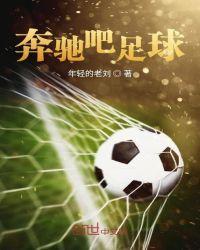笔趣阁>离婚后的我开始转运了 > 第1801章(第3页)
第1801章(第3页)
阿?握紧手机,喉咙发紧:“我们会尽快制定执行方案。每一段即将消逝的声音,都值得被郑重收藏。”
挂断电话后,她翻开工作手册,在“未来规划”一页写下新的目标:推动“家庭声音遗产计划”,联合医疗机构,在老年科、神经内科设立标准化语音采集流程,鼓励家庭在疾病初期录制亲人日常对话、朗读、哼唱等自然语音样本,用于后期情感陪伴与认知干预。
与此同时,“守护真声”系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深圳一家家事法庭首次采纳经区块链认证的儿童心声音频作为抚养权判决依据。录音中,五岁的女孩用奶声奶气地说:“我喜欢和妈妈住,因为妈妈晚上会讲故事,爸爸只会打游戏。”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法律应倾听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而非仅凭成人视角推定其利益。”
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某知名法学教授公开发文批评:“情感录音易受引导,缺乏客观性,不应作为司法证据。”舆论再度分裂。
阿?没有回避争议。她在一场直播访谈中平静回应:“我们从未主张用一段录音取代完整的法律调查。但我们坚信,一个五岁孩子亲口说出的愿望,不该被轻易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怕火灾就不许人生火取暖。关键在于如何规范使用,而不是因噎废食。”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两周,最终促成最高法出台《关于在家事案件中审慎采用未成年人陈述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在保障真实性与自愿性的前提下,允许录音、录像等形式的心理表达进入庭审参考体系。
盛夏来临,蝉鸣如织。阿?受邀前往海南参加“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创新峰会”。登机前,她在机场候机厅收到一条短信:编号HE-2024-0312账户关联案件正式宣判,施暴者获刑两年六个月,其妻弟因协助篡改证据被判拘役四个月,缓刑一年。法院特别指出:“技术手段掩盖不了人性之恶,而真实的声音终将穿透谎言。”
飞机起飞时,舷窗外云海翻涌,如同无数奔腾的思绪。邻座是个年轻妈妈,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她偷偷看了阿?一眼,轻声问:“您就是那个做‘回声车’的老师吧?我在新闻上看见过您。”
阿?点头。
女人眼眶忽然红了:“我女儿三岁时走丢了……找了八年,去年才在偏远山区找到。她被拐卖的家庭养大,根本不认我。我试了好多次想跟她说话,她都躲开……前几天,我用你们平台录了一段话,是我当年哄她睡觉唱的摇篮曲。昨天,她第一次主动问我:‘这首歌,是你以前唱给我听的吗?’”
她说着,泪水滑落:“原来……声音真的能唤醒记忆。”
阿?握住她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回握了一下。
抵达三亚当晚,主办方安排参观一处生态湿地公园。月光洒在红树林间,萤火虫在水面上闪烁。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清亮的童声合唱。阿?循声走去,竟看到一群孩子围坐在空地上,面前摆着一台便携式“回声终端”。领唱的是小舟,他身旁站着父亲,手里举着手机录像。
他们唱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歌词被改成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说就像回声一样长;
>穿过风雨和遗忘,一直回荡在心上;
>若有一天你迷路,就听这声音找方向;
>因为爱从不说散场,只会一次次回响……”
歌声飘向夜空,惊起一片白鹭。
阿?站在树影下,静静聆听。她想起离婚那天,民政局窗外灰蒙蒙的天;想起独自搬家时摔碎的茶杯;想起曾经以为人生就此黯淡无光的日子。
而现在,她站在这里,听着由痛苦孕育出的歌声,看着一个个曾封闭的心灵重新开口说话。
她终于懂了:所谓转运,不是命运突然施舍好运,而是当一个人选择不再沉默,世界便不得不开始回应。
回到酒店,她打开笔记本,继续撰写《回声行动白皮书》第三章。灯光下,她的字迹清晰而坚定:
>“我们收集的从来不是完美的声音。
>
>有结巴的道歉,有含糊的思念,有哭到破音的告白,也有犹豫许久才出口的一句‘我想你了’。
>
>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最真实的人间。
>
>当社会习惯于用结果衡量价值,我们执意守护过程中的每一次尝试;
>当成人世界崇尚冷静理性,我们坚持为脆弱与柔软保留一席之地。
>
>因为我们相信:
>每一次按下录音键的勇气,都在悄悄修补一道裂痕;
>每一段穿越时空的回音,都在重建一座通往理解的桥。
>
>而这一切的起点,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
>无论你身处何地,经历何种伤痛,
>你都有权利被听见,
>也有资格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