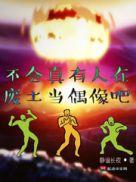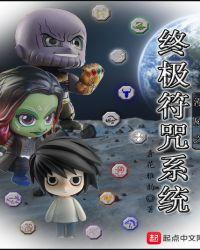笔趣阁>激荡1979! > 第505章 魏明和丽智的龙凤胎宝宝(第2页)
第505章 魏明和丽智的龙凤胎宝宝(第2页)
孟波将这段文字编入《断裂》章,并附上原始事故通报复印件??文件上“责任人”一栏空白,审批意见写着:“建议淡化处理,避免影响生产情绪。”
舆论风暴随之席卷而来。微博热搜接连三天挂着#被抹去的名字#、#她们不是辅助#、#请还她们一个称呼#。一位年轻女工程师发帖:“我在宝钢上班三年,从未听前辈提起过女子班。今天看了《拾痕录》预告片,才知道我的岗位三十年前是由五个女人轮流值夜守下来的。”
更有大批网友自发行动。山东网友组织“寻名小队”,深入鲁南矿区走访百余名老人;广州高校学生利用AI图像识别技术,从老报纸扫描件中批量提取女性工人姓名;上海一位退休语文教师义务担任校对志愿者,逐字核对五百三十七个名字的籍贯与生卒年。
就在第五辑进入最终印刷阶段时,马鞍山传来惊人消息:一位名叫周玉芬的老人主动联系项目组。
九十一岁,终身未婚,住在长江边一座孤岛上。她曾是马鞍山造船厂唯一的女电焊师,参与建造新中国首批万吨货轮。因长期吸入有毒气体,声带受损,说话含糊不清。但她坚持亲手写下一封信,字迹歪斜却坚定:
>“我不怕被人看见。我怕的是,等不到那一天。”
她随信寄来三样东西:一把用船板残片打磨的焊枪模型、一本记录每日焊接长度的日志、以及一张1971年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我们七个姐妹,说好要一起看到大海。”
可惜,其余六人均已离世。
孟波立即带队登岛。小船靠岸时,周玉芬拄拐立于岸边,风吹动她银白的发丝,像焊花飞溅时的弧光。她不开口,只是缓缓举起右手,做了个标准的焊接手势??拇指与食指圈成环,其余三指伸直。
这是当年女子电焊班的秘密暗号:**“火未熄,手不放。”**
当晚,她在油灯下翻开日志,逐页讲述那些被江水淹没的故事。说到激动处,竟用颤抖的手指蘸水在桌上画出船体结构图,精确到每一根肋骨位置。
“那时候有人说,女人干不了这行。我就焊给他们看。”她咧嘴一笑,露出几颗残牙,“我把名字焊在龙骨上,谁也刮不掉。”
临别前,她交给孟波一个密封铁盒:“等我走了再打开。里面是我六个姐妹的遗物,还有……我替她们领的奖状复印件。当年厂里发奖,只念名字,不让上台。我说不行,哪怕没人鼓掌,我也要把荣誉带回去。”
回到北京,孟波将所有新增材料紧急补录入书。第五辑最终厚度达八百二十三页,其中近三分之一为空白名录页。出版社破例采用线装加函套工艺,确保未来可增补插入新页。
出版当天,全国三十个城市同步举行“点灯仪式”。人们手持烛火,聚集在钢厂旧址、江畔码头、矿山入口,齐声朗读《她们的名字》章节。央视新闻全程直播,镜头扫过一张张苍老而坚毅的面孔,扫过一双双布满疤痕的手,扫过那一枚枚藏了半个世纪却从未示人的奖章。
而在额济纳旗那间土屋前,艾丽娅独自点燃一盏煤油灯。火苗摇曳中,她轻轻哼起《喀秋莎》。风穿过胡杨林,沙沙作响,仿佛回应。
数日后,孟波收到一封信,邮戳来自渤海湾畔一个小渔村。寄信人是孙亚男的远房侄女,称老人已于三个月前安详离世,遗嘱只有一条:骨灰撒入大海。
“她说,她不是钢,烧久了会脆。她是浪,哪怕碎了,也要往岸上冲。”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一艘老旧渔船停泊在晨曦中,甲板上摆着一只绣着“齿轮绕月”图案的枕套,旁边放着一双崭新的棉鞋??那是她最后一次为艾丽娅做的,尺码刚好。
孟波抱着照片站了很久。然后他驱车前往北戴河。海风凛冽,浪涛汹涌。他打开一只木匣,将孙亚男的胸章、日志残页、那滴干涸水痕的信纸,连同五百三十七个名字的副本,一同投入海中。
潮水涌来,卷走一切。
他站在礁石上,大声说道:“孙亚男,王桂芬,周小梅,刘素琴,赵秀兰,陈桂英,李素珍,周玉芬……你们来了!我们都听见了!”
声音被风撕碎,又被浪托起,传向远方。
回到北京后,他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新地图。不再是全国行政区划,而是由五千多个红点构成的“女性重工业劳动者足迹图”。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位已确认身份的姐姐、妹妹、母亲、妻子。
地图下方,他亲笔题写:
>**“她们不曾被看见,但从未停止发光。”**
某夜加班至凌晨,他忽然听见走廊传来脚步声。回头望去,空无一人。唯有窗外雨歇,月光洒在桌角那本《拾痕录?第五辑》上,封面上的齿轮与月亮静静旋转,宛如新生。
他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第一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