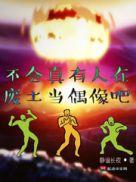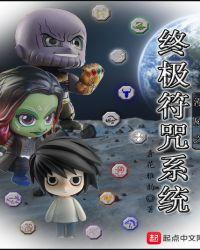笔趣阁>激荡1979! > 第505章 魏明和丽智的龙凤胎宝宝(第1页)
第505章 魏明和丽智的龙凤胎宝宝(第1页)
在伯克利生活的第一天晚上,三个年轻人都有些难以入眠,感觉新鲜劲儿还没过,尤其是两个女生,对接下来的异国求学生活既期待,又带着几分紧张。
睡不着的魏明则在罗列购物清单,最紧要的还是电脑,现在自己写。。。
雨声顺着屋檐滑落,在窗台上砸出一圈圈涟漪。孟波坐在书桌前,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封信的折痕,仿佛还能触到孙亚男掌心的温度。窗外天色灰蒙,槐花被雨水打落,铺了一地白,像极了老照片里炼钢厂飘散的炉灰。
他闭上眼,脑海却翻涌不息??那个劈柴的背影、铁皮盒中泛黄的日志、火塘边沉默的眼神……还有那句“我不是唯一活着赎罪的人”。这句话如钉子般嵌进他的骨头,越想拔,越扎得深。
第二天清晨,他拨通了艾丽娅的电话:“我要去一趟包头。”
“你真打算按她说的做?”艾丽娅声音低沉,“印厚一点,留空白?”
“不止是留空白。”孟波说,“我要让那些名字,自己走回来。”
项目组紧急调整出版计划。原定五万册首印量增至十万,纸张规格从普通胶版改为可长期保存的无酸纸。排版团队连夜重做封面内页,预留出三百页空白名录页,每一页都印有统一格式:“姓名:__________生于:____年___月___日所属班组:_________________主要事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不是空缺,是邀请。”孟波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不是替她们发声,而是为她们腾出说话的位置。”
与此同时,摄制组兵分三路,奔赴包头、攀枝花、大冶。第一站包头钢铁厂旧址,已是一片荒芜。锈蚀的高炉如巨兽骸骨矗立在风沙中,厂区大门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斑驳脱落。当地文史办提供了一份尘封档案:1978年,包头三八女子炼钢班因“技术升级”整体解散,四十三名成员全部调离一线,其中十七人被安排至后勤洗衣房,月薪削减百分之四十。
“她们连工装都没收回去。”一位退休人事科长叹气,“说是‘防止资产流失’,其实就怕她们拿去卖废铁换钱。”
但在包头郊区一间低矮平房里,他们见到了赵秀兰。八十四岁,独居,患严重尘肺病,说话断续如风箱。她从炕席下抽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块烧焦的工作牌,上面依稀可见“包钢女子突击队?赵秀兰”几个字。
“我们不是突击队,是正式编制!”她突然提高嗓门,咳出一口黑痰,“可评劳模时,名单上没我们!庆功会上,领导只提‘广大职工’四个字!”
她颤抖的手指向墙上一张合影:“你看,十二个人,全在这儿了。现在活着的,只剩我一个。”
照片里,一群姑娘戴着安全帽,站在高炉前比着胜利手势,笑容灿烂得像钢水泼洒出的光。如今,她们的脸已被岁月磨成模糊的轮廓,唯有眼神依旧锋利。
“我想上书。”赵秀兰喘着气,“哪怕一句话也好:赵秀兰,曾在一号高炉连续作业一百零八小时,没请过一天假。”
孟波点头:“您放心,这本书会等您写完。”
离开包头后,摄制组转道四川攀枝花。这里曾是三线建设的核心战场,也是全国女子炼钢班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当地老年活动中心,他们找到了陈桂英。这位曾经的“攀钢铁娘子”如今腿脚不便,靠轮椅出行,但听说《拾痕录》第五辑的事,竟执意要带他们去当年的炼钢车间遗址。
山路陡峭,轮椅由两名工作人员抬着前行。抵达山顶时,众人皆汗流浃背。陈桂英抬头望着坍塌的厂房,久久不语,忽然哼起一段歌谣:
>“金沙江水滚滚流,
>女儿扛钎上高炉。
>不求勋章挂胸口,
>只愿钢花照归途。”
这是当年攀枝花女子班自创的班歌。她轻声说:“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性别平等’,只知道不能输给男同志。冬天零下十几度,水管冻住,我们就用体温去化;煤气泄漏,没人退,因为我们知道,后面还有姐妹在等岗位。”
她在废墟中摸索许久,终于从一堆碎砖下扒出一块金属铭牌,上面刻着“1974年度先进集体?攀枝花三八炼钢班”。铭牌一角已被腐蚀,但她紧紧攥在手里,像护着最后一点火种。
“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她冷笑,“后来搞企业改制,厂史馆重新布展,我们的照片全被撤了。解说词改成‘早期以男性为主的技术骨干队伍’。可我们明明就在现场!”
回程途中,孟波接到消息:大冶那边有了突破性发现。
湖北大冶钢厂退休职工李素珍的女儿联系项目组,称母亲临终前留下一本日记,反复写着一句话:“我不是逃兵,我只是太累了。”
日记内容令人窒息。1976年某夜,高炉突发爆炸,李素珍所在班组六人中有四人当场死亡。她因提前轮休幸免于难,却被谣传为“临阵脱逃”。此后多年遭同事孤立,连子女上学都被歧视。她不敢申辩,因为事故报告被定性为“操作失误”,若追究责任,整个班组都将背上污名。
“她选择背负骂名,也要保住死去姐妹的清白。”女儿哭着说,“可她一辈子都在梦里跑警报,喊‘快撤!快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