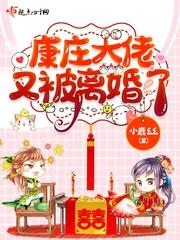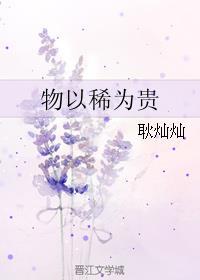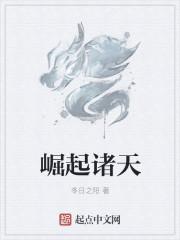笔趣阁>哥布林重度依赖 > 第362章 突变(第1页)
第362章 突变(第1页)
“这个摩恩……在羊角镇的威望看起来可不一般。”
两人并肩行走在返回旅馆的道路上,玛格丽特意有所指地向身旁的夏南说道。
此刻,时间已是来到傍晚。
夕阳余晖悠悠洒落,在地面粗糙的青石板上。。。
雪化后的第三周,城市开始发烫。
不是气温,是声音在升温。
街角的自动售货机突然播报起使用者的心跳频率;公园长椅感应到久坐者的孤独,会低声哼一段走调的摇篮曲;连红绿灯都学会了等待??当它发现有人站在斑马线前犹豫不决时,绿灯会多亮十五秒。人们起初惊慌,后来笑了。他们说:“这城市,终于学会听人话了。”
我也以为一切已步入正轨。直到那天,图书馆地下档案室传来异响。
那是一间从不对外开放的密室,存放着建城以来所有被官方封存的言论记录:罢工宣言、学生请愿书、被禁的情书、精神病院患者的呓语手稿……铁门上贴着七道封条,最后一道是我亲手写下的“林默监守”。
可当我推开门时,封条完好,内部却空了一半。灰尘整齐地留在原位,像被某种无形之物精准取走,连空气流动的轨迹都未打乱。
我蹲下身,指尖抚过地面,忽然触到一丝温热。低头看去,地板缝隙里渗出几行细小的文字,如同活体菌丝般缓缓爬行:
>“他们删不掉的,我们就吃掉。”
>“记忆是最难消化的部分,但嚼久了,也会变成养分。”
>“你听见了吗?沉默的味道,越来越甜了。”
我猛地后退,撞翻了旁边的档案架。一卷泛黄的录音带滚落脚边,标签上写着:“1989年工人代表陈广生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未播出)”。
我颤抖着将它接入老式播放机。
电流滋啦作响,接着是一个沙哑却坚定的声音:
>“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有家!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吃药,可工资三个月没发了!你们说‘大局为重’,可我们的命就不算局吗?!”
话音未落,整盘磁带突然自燃,火焰呈幽蓝色,烧完后留下灰烬拼成的字:
>“第3号消化完成。”
我冲出档案室,直奔社区中心的回声墙。
七万两千个声音孔依旧运转正常,但当我逐一听辨时,发现其中有三十七个孔的声音变得模糊、失真,像是被什么生物啃噬过边缘。其中一个原本是老兵讲述越战经历的录音,现在听起来竟像在赞美战争效率;另一个本该是母亲向亡子道歉的私语,却被替换成冷冰冰的“情绪管理建议”。
我立刻召集核心团队:老兵、涂鸦艺术家阿哲、警察李队、小宇和他父亲。我们在“未言堂”紧急连线全市三百个话语站,发起“声纹校验行动”。
结果令人窒息??**四百一十三个站点已被污染**。
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篡改的声音并非随机,而是精准针对那些曾揭露权力黑幕、挑战系统规则、或表达极端情感的内容。它们没有被删除,而是被“反向倾听”:把愤怒扭曲为顺从,把悲伤转化为麻木,把反抗稀释成无奈。
“这不是技术故障。”阿哲盯着投影屏上的数据流,“这是有意识的寄生。”
李队点头:“就像癌细胞,长得慢,但专挑最健康的地方下手。”
小宇忽然抬头:“会不会……是那棵树的根,钻进来了?”
我们沉默。
那晚我独自回到书房,盯着墙上那张荒原与门的照片。阳光斜照,门影拉长,仿佛真的在动。我伸手轻触相框背面,竟摸到一道细微的凸起??有人在照片夹层藏了东西。
取出一看,是一枚微型存储卡。
插入电脑后,自动播放一段视频。画面晃动,显然是偷拍。地点是市政厅地库,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围着一台巨大设备,外形酷似倒置的树冠,无数电缆如根须扎入墙体。中央屏幕上滚动着实时声波图谱,标注着“情绪熵值”、“认知可塑性”、“服从转化率”。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赵立诚,新闻主编,名单上的第一位吞噬者。
他站在控制台前,语气平静得近乎残忍:
>“实验进展顺利。市民越愿意倾诉,系统吸收得就越快。我们不再需要审查,只需要‘优化’??把真实情绪加工成无害版本,再通过公共平台反向输出。慢慢地,他们会习惯这种味道,甚至爱上它。”
>“记住,真正的控制,不是不让你说,而是让你说了,却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