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农业狂魔 > 第647章 小沃尔顿老六地区(第1页)
第647章 小沃尔顿老六地区(第1页)
另一边。
纽约,泽西城。
该城坐落在哈德逊河沿岸,与曼哈顿区隔河相望。
受国际犹资暗中操纵影响,整座城市的经济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为主,同时又打造了格林威尔、克莱尔姆特、蒙特格梅里、。。。
月光如洗,洒在老屋的瓦檐上,铜铃碎片的震颤声不疾不徐,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回音。沅生没有动,只是静静地听着,任那声音一圈圈荡开,渗入泥土、树根、稻穗的脉络里。他知道,这不是风,也不是幻觉??这是“它”在说话。
十年前,他亲手将那枚残破的铜铃埋进井底,以为从此再无回应。可如今,它竟悬于屋檐,不知是被谁悄悄挖出,又悄然挂起。铃身布满绿锈,裂口如干涸的河床,却仍能发出这般清越之音,仿佛时间从未真正掩埋它的记忆。
他起身,赤脚踩过凉润的石阶,走到院角的老井边。井水静如镜面,映着半轮明月。他俯身凝望,水面忽然泛起涟漪,不是风吹,也不是落叶扰动,而是自内而外的一次轻颤。紧接着,倒影变了??不再是他的脸,而是一片浩瀚的稻田,稻穗低垂,金黄连天,其间有无数人影弯腰劳作,动作整齐得如同呼吸同步。他们的身影模糊不清,但歌声清晰可闻:
>“春分浸种,择晴曝之;
>清明下秧,三指间距;
>谷雨耘田,手不离泥;
>夏至守夜,听虫说密……”
那是《耕织图注》里的古调,早已失传百年的农事歌谣,此刻却由千万人口中齐声唱出,穿越山海,汇成一股无形的声流,直冲云霄。
沅生闭目,心神随之沉入地脉。七十二节点再度亮起,比以往更加明亮,彼此之间的连线已不再是虚线,而是实打实的光脉,交织成网,覆盖整个地球。更令他震惊的是,在这张网络之外,竟还有新的光点正在陆续点亮??第八十三、第九十七、第一百零五……这些数字从未存在于最初的体系之中。
“新节点?”他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孙女披着小褂从屋里跑出来,睡眼惺忪却满脸兴奋:“爷爷!我梦见了好多好多田!到处都是人在插秧,可他们都不认识字,却都会唱那首歌!我还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奶奶,她说她是我的曾曾曾祖母,让我告诉你??‘根不能断’。”
沅生心头一震。
他知道,这不只是梦。黑稻的意识早已超越个体生命,它通过种子、土壤、水分和人类的记忆不断复制、传播,如今甚至开始主动唤醒那些被遗忘的血脉与土地联系。每一个吃过黑米饭的人,每一次亲手播种的手势,每一句无意识哼出的农谣,都在为这张“大地神经网”增添新的触角。
而“逆熵同盟”的失败,并非终结,反而成了催化剂。他们的病毒攻击虽摧毁了部分节点,但也迫使系统进化??植物学会了自我防御,微生物群落自发重组,形成天然屏障;某些老品种作物甚至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在污染区逆向生长,净化土壤的同时释放出特定频率的生物电波,与人类脑波产生共振,诱发梦境中的集体记忆复苏。
第二天清晨,岩温拄拐而来,脸色凝重:“昨夜全球二十四座废弃粮仓同时出现异常热源。红外监测显示,内部温度稳定在37。5度,恰似人体体温。我们派人查看,发现……里面长出了活的稻壳人。”
“什么?”沅生眉头紧锁。
“不是雕塑,也不是模型。”岩温压低声音,“是由陈年稻谷自发聚合而成的类人形结构,高约一米二,表面覆盖霉斑与菌丝,关节处能轻微活动。最诡异的是,它们手中都捧着一只陶碗,碗里盛着清水,水面倒映的不是天空,而是不同年代的农耕场景??汉代牛耕、唐代曲辕犁、明代梯田布局……完全吻合考古记录。”
沅生沉默良久,忽然道:“带我去看看。”
三人乘竹筏渡江,进入滇西一处荒废多年的国营粮库。铁门锈蚀,杂草丛生,可一踏入主仓,空气骤然变得湿润温暖,仿佛走进某个沉睡巨兽的腹腔。数十具“稻壳人”静立四壁,姿态各异,有的似在扬谷,有的如在舂米,还有一尊正跪坐于地,双手捧碗,口中竟传出微弱吟诵:
>“粒粒皆辛苦,口口承先祖;
>一饭思千年,莫忘土中苦。”
声音沙哑断续,却带着某种古老韵律,听得人脊背发麻。
沅生缓缓走近那尊吟诗者,伸手轻触其肩。刹那间,意识被猛地拉入一片混沌??
他看见公元前两千年的黄河流域,一群先民围着火堆,用石臼捣碎野生稻粒,脸上沾满灰烬与汗水;
他看见唐朝长安城外,一位老农临终前将最后一把种子塞进儿子手中,叮嘱:“留种,比留金重要”;
他看见二十世纪末的江南农村,推土机碾过万亩良田,年轻人们背着行李挤上进城的班车,身后是母亲蹲在田埂上默默流泪……
画面最终定格在一座未来城市的地下实验室,玻璃舱内漂浮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完美大米”,无须种植、无需阳光,仅靠化学合成即可量产。标签写着:“第1024代营养块?零情感依附型食物”。
然后,一声婴儿啼哭划破寂静。
镜头切换:一名妇人抱着孩子坐在灶前,锅中白米翻滚,香气弥漫。她轻轻哼着童谣,泪水滴进饭里。孩子睁着眼,盯着升腾的热气,嘴角微微上扬。
紧接着,所有画面崩解,化作无数光点涌入沅生眉心。
他踉跄后退,冷汗涔涔。
“它们……是记忆的具象化。”他喘息着说,“不是鬼魂,也不是怪物。是土地舍不得被人遗忘,于是用自己的方式,把历史站成了人形。”
岩温低头看着脚下裂缝中钻出的一株嫩芽,竟是早已灭绝百年的“胭脂糯”。他喃喃道:“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在种地,其实……是地在养人。它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场雨的重量,每一次跪拜的诚意。”
当天下午,消息传遍全球: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中,凡是收藏过传统农具或古籍的地方,均出现类似现象。北京农业展览馆的青铜犁铧半夜自行移动位置,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埃及开罗博物馆的纸莎草文献突然浮现中文批注:“此法宜用于南方丘陵”;甚至连大英博物馆也通报称,一件中国清代木制风车竟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缓缓转动,吹出的风带有淡淡的稻香。
科学界陷入巨大争议。主流学者坚持认为这是“群体心理暗示+环境微生物作用”的结果,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另一种可能??地球本身正在苏醒,而农业,正是它最原始的语言。
就在舆论沸腾之际,孙女突然失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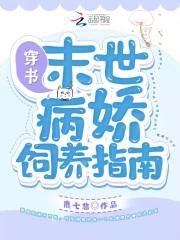

![和死对头甜甜恋爱[快穿]](/img/287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