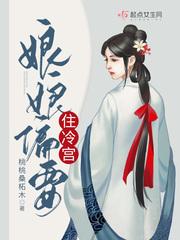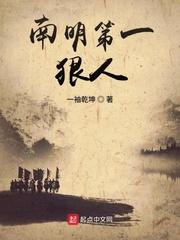笔趣阁>大宋为王十三年,方知是天龙 > 第375章 夜战八方(第1页)
第375章 夜战八方(第1页)
大宋营盘四周都修有工事,壕沟陷坑绊马索,沟内坑中则撒放尖石木刺铁蒺藜。
涿州兵马正在假意破除这些,前面弓箭掩护,后面军丁搭木板,洒黄土,垫放干草苇絮。
可是却动作缓慢,出工不出力,显然是虚。。。
赵曜自西北归来,朝堂之上虽一时风平浪静,然他深知,真正暗流汹涌的战场,不在边疆,而在庙堂。
王文昭伏诛,旧贵族与清流派虽受重创,却并未彻底瓦解。赵曜在朝会上宣布新政再推,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势力。此令一出,朝中顿时哗然。
“陛下!”兵部尚书陈仲甫出列,声音沉稳却透着不满,“新政虽利国,然若操之过急,恐伤民力,动摇根基。臣请陛下三思。”
“三思?”赵曜冷笑,“陈尚书,你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可曾真正为民思虑?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朕若不改革,大宋将何以为继?”
陈仲甫面色微变,低头不语。
赵曜目光扫过群臣,缓缓道:“朕已命户部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田,凡隐匿田产者,一律抄没。凡侵占民田者,严惩不贷。”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许多旧贵族出身的官员面色大变,皆知新政一旦推行,他们赖以维系的根基将被彻底动摇。
散朝后,赵曜召沈若兰入御书房。
“陛下,臣已查明,陈仲甫与旧贵族赵氏仍有往来,且其子陈景明,与江南豪族多有勾结。”沈若兰低声禀报。
赵曜沉吟片刻,缓缓道:“陈仲甫虽非主谋,但若不除,恐成后患。朕欲借清查隐田之机,将其一并拿下。”
沈若兰拱手道:“陛下圣明。然此举若操之过急,恐引发朝中动荡。”
赵曜目光坚定:“朕已非昔日之赵曜,既然要改革,便必须彻底。若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沈若兰点头:“臣即刻安排。”
数日后,户部正式展开清查行动,密探司与御史台联手,对地方豪强展开大规模调查。陈仲甫之子陈景明被查出私占良田千顷,且与江南豪族勾结,意图阻挠新政。
赵曜震怒,下旨将陈景明抄家问罪,并将陈仲甫革职查办。
此事震动朝野,旧贵族与清流派人人自危。
与此同时,赵曜命沈若兰秘密调查朝中与赵承业、王文昭有往来之人,务必一网打尽。
沈若兰领命而去,数日后,果然查出朝中尚有数位旧臣与赵承业有密信往来,其中竟包括礼部侍郎李元甫。
李元甫乃前朝老臣,素以清流自居,曾多次在朝中公开反对新政。赵曜虽知其心怀不满,却未料其竟与赵承业暗中勾结。
赵曜召李元甫入宫,亲自审问。
“李元甫,你可知罪?”赵曜冷声问道。
李元甫面无惧色,昂首道:“臣不知陛下所指何罪。”
赵曜将密信甩至他面前:“这些密信,可是你与赵承业所书?你若否认,朕可当场令你亲笔对照。”
李元甫脸色微变,但仍强辩道:“臣与赵承业乃旧识,偶有书信往来,亦属寻常。”
赵曜冷笑:“寻常?你可知赵承业勾结西夏,意图谋反?你若不知,为何密信中提及‘新政害民,当除之’?你若无辜,为何赵承业伏诛后,你却秘密遣人前往江南?”
李元甫沉默片刻,终是长叹一声:“陛下圣明,臣无话可说。”
赵曜缓缓起身,道:“朕念你曾为先帝旧臣,亦曾为国效力,本可留你一命。然你若继续包藏祸心,朕亦不介意送你与王文昭同赴黄泉。”
李元甫跪地,面色惨白,良久方道:“臣……愿交出所有证据,供出所有同党。”
赵曜点头:“很好。沈若兰,即刻提审。”
沈若兰领命而去,数日后,果然从李元甫口中审出朝中尚有十余位旧臣与赵承业、王文昭有往来,且暗中策划另立新君,意图推翻新政。
赵曜大怒,下旨将涉案之人全部革职查办,并将主谋三人斩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