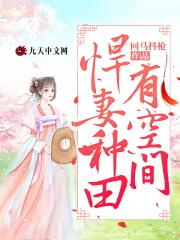笔趣阁>女尊首辅养成记(科举) > 3440(第16页)
3440(第16页)
nbsp;nbsp;nbsp;nbsp;小到面圣见礼的姿势,大到入场顺序,事无巨细都交待清楚。一晃眼的功夫,一天时间就过去了。
nbsp;nbsp;nbsp;nbsp;傍晚出宫,夕阳下春风夹着暖意扑面而来,经过这一天的相处,士子之间熟了许多,出宫时不少人都相互低声交谈。
nbsp;nbsp;nbsp;nbsp;张珏满脸漠然地走在最前面,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便没人找她说话。她看到杨思焕也只是掠过一眼,就好像看到一个陌生人。一整天,两人之间一句话也没说。
nbsp;nbsp;nbsp;nbsp;杨思焕回到客栈时,夜已深,掌柜的给她开门才知道她今日进了宫,老人家好奇地问:“小官人,紫禁城里是什么样的?那砖块可是金子做的?”
nbsp;nbsp;nbsp;nbsp;杨思焕揉了揉眉心,笑道:“寻常砖罢了。”
nbsp;nbsp;nbsp;nbsp;她这一整天都是提心吊胆,唯恐出了差错,根本不敢四下张望,至于里面什么样,她也记不清了。
nbsp;nbsp;nbsp;nbsp;殿试的前一日,杨思焕雇了一辆马车,当夜就出发在宫外不远处等着,在车里睡了一觉。
nbsp;nbsp;nbsp;nbsp;丑时三刻,不少士子已经侯在宫门外,虽是暮春,早上还是有些凉,杨思焕穿了件长衫,外面披了件披风。
nbsp;nbsp;nbsp;nbsp;不到卯时门就开了,士子们依次排好队,由专人搜检一番才放行,快到杨思焕时,她自觉地脱下披风。那日司仪交待过,面圣要穿得正式,况且披风容易藏夹带,也是不允许带的。
nbsp;nbsp;nbsp;nbsp;经过检查之后,鸿胪寺的人过来将她们领走。
nbsp;nbsp;nbsp;nbsp;朱红的宫墙像盘龙向前延绵,氤氲的晨雾中,一眼望不到头。
nbsp;nbsp;nbsp;nbsp;殿试考时务策,策问由内阁大臣们拟好题目,交给皇帝钦定,一般涉及吏治政风、民生仓储等,二三百字。饶是如此,策问几乎无关国是,考察的都是士子治国理政的能力,不会涉及重大决策。
nbsp;nbsp;nbsp;nbsp;士子收到策问之后写对策,格式固定,不许涂改,且不得少于一千字。杨思焕这些天看了不少状元的对策,很少有状元写的对策少于两千字的,总得来说,尽量写多一点。
nbsp;nbsp;nbsp;nbsp;杨思焕走在路上,双手不停地抓握,现在她的双手冰凉,甚至有些僵,怕只怕到时候连笔都拿不稳。
nbsp;nbsp;nbsp;nbsp;鸿胪寺的人将士子们带到太和殿,两廊已经整齐地排好了二尺高的书案,旁边铺着明黄的蒲团,杨思焕见状不由地蹙眉。
nbsp;nbsp;nbsp;nbsp;果然没猜错,要跪着答题。考试要考一天,她就得跪一整天。
nbsp;nbsp;nbsp;nbsp;士子跪好,片刻后出来一个宦官,朗声道:“皇上驾到。”
nbsp;nbsp;nbsp;nbsp;众人闻声纷纷低下头,周遭一片死寂,余光中,皇上身着明黄的衮冕朝服,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向龙椅。
nbsp;nbsp;nbsp;nbsp;士子们行了三叩礼,礼部侍郎就带人过来散题。
nbsp;nbsp;nbsp;nbsp;散题时,太阳已经升起,阳光泄入殿中,也没那么冷了。
nbsp;nbsp;nbsp;nbsp;题目装在牛皮纸袋里,开口处盖了衿章,杨思焕轻呼一口气,拆开信封,当题目在她手中展开时,她怔了怔,随之皱了眉。
nbsp;nbsp;nbsp;nbsp;第40章第四十章殿试
nbsp;nbsp;nbsp;nbsp;策问是内阁大臣出,之后交给皇帝钦选的,能进内阁的,哪一个不是人精?她们出题自然是讲究的。
nbsp;nbsp;nbsp;nbsp;往年的策问内容,无非是安民、兴贤、吏治,这是倒好办。
nbsp;nbsp;nbsp;nbsp;有时也会出抽象的,抽象的分为两大类,其一守成,其二开拓。
nbsp;nbsp;nbsp;nbsp;杨思焕看过无数状元对策,总结出模版,前者的对策套路,就是夸颂扬当今圣上英明的同时,顺带在原有制度上提一点小建议,要想出彩,关键就在这小建议上,既不能戳了圣上的心,又不能言之无物。
nbsp;nbsp;nbsp;nbsp;而后者的套路也差不多。总之就是,边夸边提意见,重要的是知进退,懂方寸。
nbsp;nbsp;nbsp;nbsp;但今天的题似乎和以前不一样,题目开篇就是:暴雪连天,累及南北,饿殍遍野,房屋倾颓…
nbsp;nbsp;nbsp;nbsp;开篇描述得很是惨烈,简单来说,就是连日大雪,压倒房屋、冻死百姓,其中还有不少是被饿死的。
nbsp;nbsp;nbsp;nbsp;最后连发三问,首先问如何赈灾,又问如何治理,最后一问很奇怪,问的是:谁应该为此事负责?
nbsp;nbsp;nbsp;nbsp;整题以雪灾为载体,看起来考治灾,但再看最后那句:卿以为,孰当担此责?
nbsp;nbsp;nbsp;nbsp;这种问法杨思焕倒是头一回见,她将题目反反复复读过一遍,先不急着打草稿,而是揣测皇上的意图,以及那位出题的内阁大臣的意图。
nbsp;nbsp;nbsp;nbsp;当朝内阁六大辅臣,她虽然不知道是哪六位,但按理来说,能入内阁的,至少是四十多岁,甚至七八十也有可能,她们那些老家伙浸淫宦海多年,心思太难猜了。
nbsp;nbsp;nbsp;nbsp;她就从皇帝那边考虑。皇帝当然希望安定民心,灾难来临之际,很多百姓会把原因归结于神明,君权神授,据说十几年前关中旱灾,一个多月不下雨,饿死了不少人,先皇便带着太女在应天开坛祈雨,又斋戒了两日。
nbsp;nbsp;nbsp;nbsp;当然,她才不会傻到说皇上有错,千错万错只能是下面人的错。
nbsp;nbsp;nbsp;nbsp;她想了想又觉得不妥,她作为新科贡士,什么作为都没有,难道她要长篇大论来批判六部?想想就觉得文风很怪。
nbsp;nbsp;nbsp;nbsp;皇上问谁该当此责,她答题应该把自己放在臣子的位置上,这样一来,这哪里是问责?分明是换着花样问怎么完善制度,因为只有完善了制度,各部才能更好地运作。
nbsp;nbsp;nbsp;nbsp;想到这里,她猛然惊醒,差点会错意了。
nbsp;nbsp;nbsp;nbsp;于是,她提笔开始写大纲,首先是赈灾,雪灾赈灾无非是着户部放粮施粥,江南是天下粮仓,一般不会挨饿,因此这部分得先考虑北方,尤其是本朝建国不到百年,北方尚未完全平定,稳住民心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