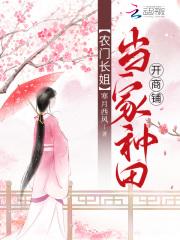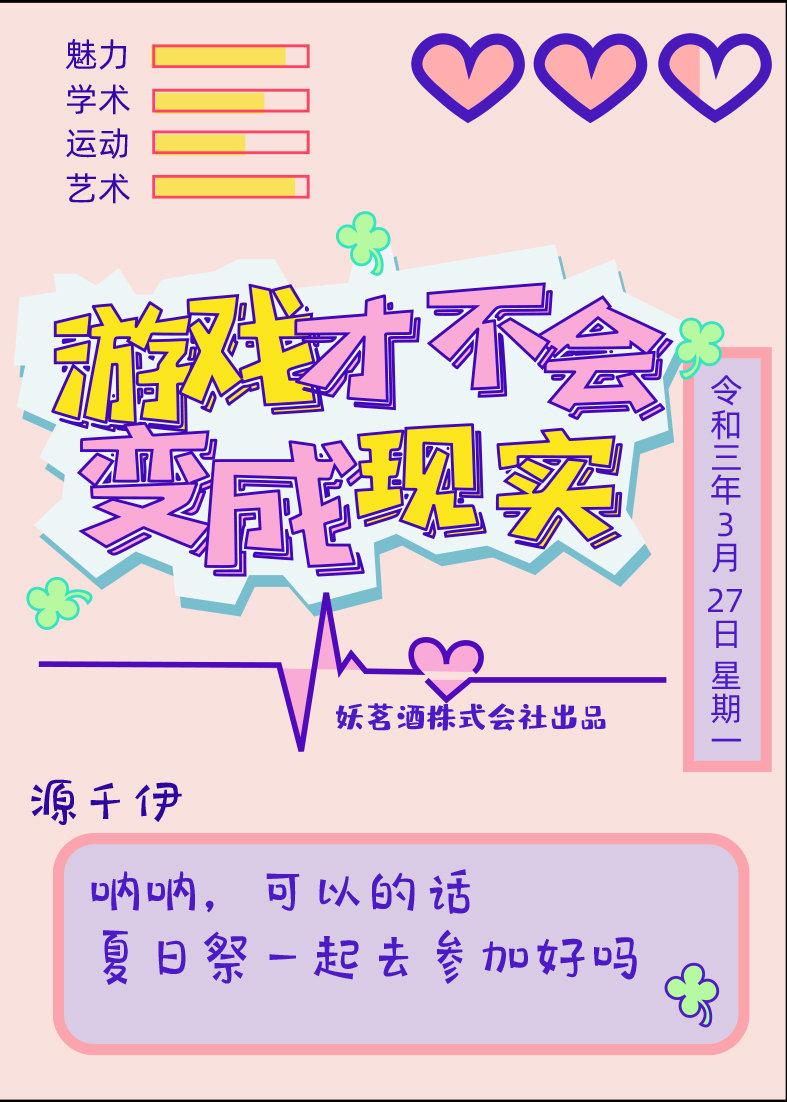笔趣阁>和闺蜜嫁进侯府吃瓜看戏(穿书) > 165第 165 章(第3页)
165第 165 章(第3页)
沈令月扶住她:“累了?”
她摇头:“不是累,是……太满了。这些声音,这些光,压得我几乎站不住。”
沈令月轻笑:“那就靠着我吧。当年你说要办女塾时,我也是这样扶着你走过第一场风雨。”
数日后,阿菱如期启程赴西域。临行前,她带来一块新制的旗帜??丝绸质地,绣着并蒂莲花,中间嵌着汉、龟兹双语铭文:
**她来?她亦**
燕宜亲自为她系上肩带:“一路平安。”
阿菱回头一笑:“等我回来时,要带十个西域姑娘来念书。”
春风浩荡,驼铃远去。
而燕宜并未停下脚步。她开始筹划“盲女学堂”,专收视障女子,采用凸点文字教学;又联合医者编写《女子病理图谱》,打破“女病难言”的禁忌;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竟提议设立“女子议政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各地推选代表共商民生大事。
有人讥讽:“女子连官都做不得,谈何议政?”
燕宜答:“从前说女子不能读书,现在呢?从前说女子不能行医,现在呢?从前说女子不能航海,现在呢?一步步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坐在朝堂之上,亲手写下法律。”
夏日某日,她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一本尘封日记??竟是十年前初办学堂时所记。翻开第一页,稚拙笔迹写道:
>“今日招得三名学生,皆农家女。教她们写‘我’字。阿春总把那一撇写成捺,我说不对,她红着眼说:‘可我一直都是别人家的丫头,从来没当过我自己。’”
燕宜合上本子,久久无言。
当晚,她提笔写下新的碑文,命人刻于书院后山:
>“此处未曾埋骨,却葬着无数未曾出生的梦想。
>但今日之花,已非昨日之种。
>我来,故她在。”
秋收时节,第一批“流动女塾”归来汇报。老师们带回厚厚的教学记录,还有山村孩子们亲手绘制的图画??有画先生讲课的,有画自己读书的,更有孩子画了一扇大门,上面写着“欢迎女生进来”。
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封来自北方小村的信。信纸粗糙,墨迹斑驳:
>“先生:
>我们村原先不让女孩上学,说‘读了书要造反’。可自从您派来的张老师住了三个月,现在全村女童都能背《百家姓》了。昨天村长孙女指着太阳说:‘爷爷,你看,那是阳,不是男!’全村人都笑了。
>我们想请您来看看。哪怕只站一会儿也好。”
燕宜读罢,泪落纸上。
她决定亲自前往。
临行前夜,她再次登上高楼。月色如练,照见庭院中那面绣着“她来”的小旗静静飘扬。她取出苏砚遗留的黑白画像,轻轻放在窗台。
“你看见了吗?”她whisper,“她们真的来了。”
风穿窗而入,吹动画角,那枚梅花印记微微晃动,仿佛回应。
翌日黎明,燕宜束发行装,杖头“前行”二字迎光生辉。她跨上马车,挥手告别。
车队驶出城门时,整座苏州万人空巷。百姓夹道相送,手中举着写满名字的纸片,高呼:
“燕先生慢走!”
“替我们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告诉每一个小禾??你可以!”
燕宜掀帘回望,只见书院匾额在朝阳下熠熠生辉,而桃林深处,万千名字随风轻响,如同大地的心跳。
她闭目,轻语:
“执笔者不死,因她始终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