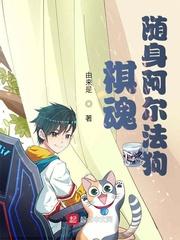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大隋刚登基,你说这是西游记 > 第496章 九尾狐谢家香火(第3页)
第496章 九尾狐谢家香火(第3页)
于是,一场新的行动开始了。
阿福下令开启“忆井直播”??每逢朔望之夜,由守心者轮流值守井畔,通过铜铃共鸣,将某段真实记忆投射于夜空,供万人共观。有人看到母亲临终前未能说出的遗言,有人看见祖先为正义赴死的背影,还有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家乡曾埋葬过上百具无名尸骨。
与此同时,小全子牵头创办“记忆学堂”,邀请曾受害者的后代与加害者的子孙同堂听课。起初冲突不断,有人怒吼“你们家族欠我们血债!”,也有人反驳“我爷爷也是被逼的!”可渐渐地,争吵少了,倾听多了。有人开始交换家族信物,有人共同为逝者立碑。
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岭南。两名少年??一人为当年刽子手之孙,一人为被斩忠臣之后??在课堂上激烈争执后,竟相拥而泣。次日,他们一同来到忆源塔,合力点燃一盏双芯纸灯,灯上写着:“我们不想再恨,也不想再逃。”
这一幕被画成新图,悬于塔内第六层。
而在这场觉醒的浪潮中,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在皇宫。
新帝某夜独自巡阅《实录补遗》,读至“永昌七年,户部虚报粮储,致河北饥民易子而食”一段时,突然掩面痛哭。他连夜召见阿福,哽咽道:“朕虽未亲历,却是这罪孽的继承者。若不赎,何以为君?”
次日,他颁布《承罪诏》,宣布今后每任皇帝登基,必须先赴忆源塔诵读《守心铭》,并在“赎罪碑林”中为自己前任的过错献上一盏灯。此外,皇室每年拨出三成内帑,用于扶持民间记忆传承项目。
此举震动天下。有贵族讥讽“帝王行奴仆之事”,可百姓却纷纷叩首流泪。一位老农拉着孙子说:“孩子,你看,连皇帝都在认错,咱们还有什么好躲的?”
人心,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撬开。
至于“无忧教”,终究未能成势。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面伤痛而非麻痹自我时,那些所谓“无忧丹”便失去了市场。最后一批传教士被捕时,供出幕后主使竟是几名前朝遗老,他们不甘权力失落,妄图借“遗忘”重建权威。
审判之日,阿福亲自主持。她没有判他们死刑,而是命其终生劳役,参与修建“记忆长城”??一条贯穿南北的石道,沿途设立三百六十座忆井亭,每一座都刻有一位普通百姓的名字与故事。
“你们想抹去历史?”她说,“那我就让历史铺满大地,踩在每个人的脚下。”
多年后,travelers行至此处,常驻足抚摸那些粗糙的石碑,读着上面平凡却动人的话语:
>“王氏,织女,活了六十三岁,最爱春天的桃花。”
>“陈二狗,挑夫,救过三个落水娃,自己不会游泳。”
>“柳婆子,寡妇,养大七个孤儿,最后一个考上了功名。”
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英雄,但他们终于被记得。
又一年春,终南山梅花再度盛开。
阿福已不再频繁行走天下,而是留在塔中整理史料,撰写《守心志》。念生依旧时常出现,有时帮她研墨,有时只是坐在檐下吹笛。没人知道他究竟是魂是影,是愿是执,但阿福知道,只要还有人点亮纸灯,他就不会真正离开。
那一日,她收到一封信,来自极北苦寒之地。信纸粗糙,字迹歪斜:
>“阿福姑姑:
>我是小全子的侄女,在这边陲小镇做医女。前些日子来了个疯老头,嘴里一直念叨‘对不起孩子们’。我问他谁的孩子,他说‘祭坛里的’。我吓了一跳,可后来查档案,发现这里百年前真是个人祭转运站……
>我给他治了病,还陪他去了附近一座荒坟,烧了纸钱。回来的路上,他哭了,说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
>姑姑,原来记住,真的能治病。”
阿福读罢,久久无言。她走到塔顶,望着远方绵延的山河,轻声说道:“念生,你说得对。救赎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风起,铃响,万千心灯在人间闪烁,如同永不熄灭的星辰。
这场雪,确实从未结束。
但它已不再是哀悼的象征,而成了行走的见证??
每一步落下,都是对遗忘的抵抗;
每一次呼吸,都是对生命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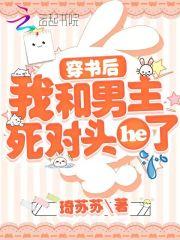
![曹操是我爹[三国]](/img/9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