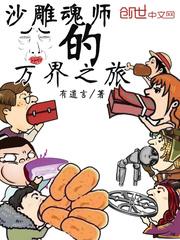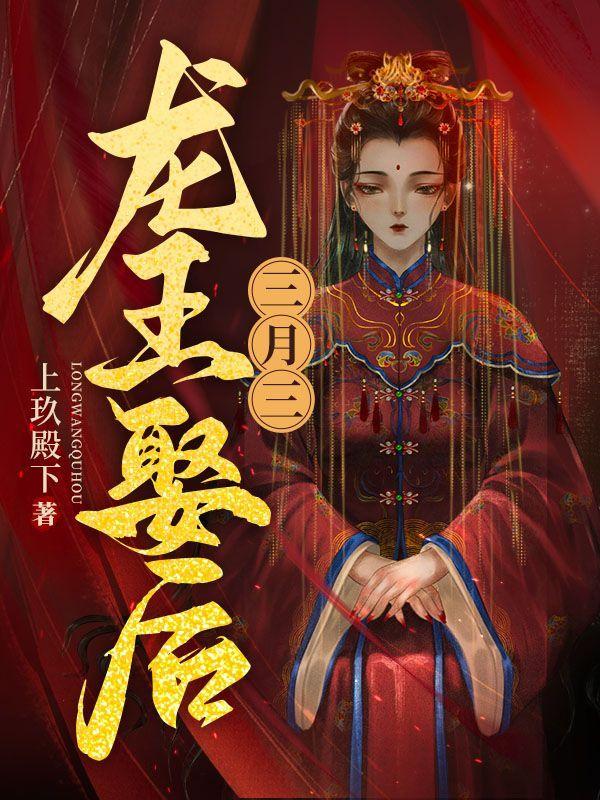笔趣阁>相国在上 > 252点到即止(第1页)
252点到即止(第1页)
淮安府城,漕运总督衙门。
“桑帮主今天怎么有空到老夫这里来?莫不是来打秋风的?”
总督蒋济舟坐在太师椅上,含笑望着对面的漕帮帮主。
桑世昌年过五旬,身材不算高大但颇为精壮,面容好似刀。。。
春风拂过朔州城头,柳絮如雪般飘落,落在李昭肩头,又轻轻滑下。他仍坐在那张旧椅上,手中握着一杯冷茶,目光却穿透夜色,望向并州方向的天际线。那盏烽燧台上的孤灯,在晨光熹微中渐渐黯淡,却始终未熄。
自“靖安司”覆灭、沈砚留任以来,朝堂看似重归平静,实则暗流未绝。皇帝虽下旨裁撤监察机构,然御史台余党犹存,六部之中仍有数名高官与前裕王旧部藕断丝连。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份曾流入民间的伪诏原件??笔迹确凿,印鉴清晰,竟在三日后神秘失踪,连藏匿副本的密档房也被人焚毁一空。
李昭知道,这并非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
三日后,崔元朗急报:代州边境发现一支无名骑兵,约三百人,皆披黑甲,面覆铁帷,行踪诡秘,不劫百姓,不扰驿站,唯沿长城旧道北行,直趋漠南。其军旗残破,隐约可见一个“松”字逆纹绣于其上,与当年程文谦案中所见符记如出一辙。
“他们还在。”李昭低声喃喃,指尖轻敲案角,“不但没死,反而……脱壳重生了。”
他召来鹰扬营统领刘三,命其即刻率精锐潜入漠南查探,不得交战,只许追踪。临行前,他取出一枚铜牌,上刻“影归”二字,交予刘三:“若遇穿素袍者,无论生死,持此牌示之。记住,不可妄动杀心。”
刘三领命而去。
半月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京城传来消息:沈砚病重卧床,已连续七日未上朝。有传言称,皇帝私下召见三位阁老,密议“易相”之事;更有风声说,一名来自西蜀的道士入宫三日,献《天机录》一部,言“宰辅气运将尽,唯换血方可延国祚”。
李昭听罢冷笑:“换血?是要把忠骨熬成汤药,喂给那些躲在暗处的豺狼罢了。”
当夜,他独步至城南陋巷,欲再访盲琴师,却发现那间破屋早已人去楼空,仅余半截断弦悬于梁上,随风轻晃,发出细微嗡鸣。墙角石缝间,压着一张泛黄纸条,墨迹潦草:
>“鹤唳已过,雾未散。
>松根深埋地底,待雷而动。
>若君尚存信念,请赴雁回坡古庙,焚香三炷,读《礼运大同篇》一遍。
>??无妄留。”
李昭默然良久,翌日清晨便轻装简从,独自策马前往代州边界。
雁回坡古庙荒芜依旧,枯井旁杂草丛生。他依言焚香,跪于残碑前,一字一句诵读《礼运大同篇》。诵毕,忽觉脚下地面微颤,似有机关松动之声自井底传来。
他俯身探看,只见井壁青砖竟缓缓移开,露出一道暗格。内藏一卷羊皮地图,边缘焦黑,似经火焚后抢救而出。展开一看,竟是整座大周疆域图,但不同于官方舆图,此图之上遍布红点与细线,勾连南北要道、粮仓、兵站、驿站,尤以北方七镇为核心,标注密密麻麻的“转运节点”“隐户屯田”“私铸工坊”,甚至还有几处写着“傀儡官员姓名”。
而在地图正中央,朱砂圈出一座宫殿轮廓,旁书四字:
**紫宸为渊。**
李昭心头剧震。
紫宸殿乃皇帝居所,何以被称作“渊”?难道……真正的执棋者,并非“靖安司”,也不是哪位权臣,而是那个一直端坐龙椅、看似中立裁决的人?
他猛然想起沈砚诗中信末所言:“汝守孤城日,吾在紫宸班。”当时以为是象征性说法,如今看来,或许正是警示??**沈砚早已察觉帝王之心偏移,却因身份所限,只能以隐语相告。**
正在此时,庙外马蹄声起。
一骑飞驰而来,马上之人满身尘土,左臂缠布渗血,正是失踪已久的刘三。他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声音嘶哑:“将军……属下找到了……赵破军。”
李昭瞳孔骤缩。
“他在漠南一处废弃军寨中,身边仅有十二名老兵,皆戴铁面,不言不语。他们守护着一口青铜棺,棺上刻着‘影归真处’四字。我靠近时,赵破军现身拦路,面容依旧狰狞可怖,但他摘下面具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