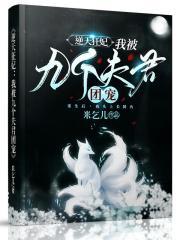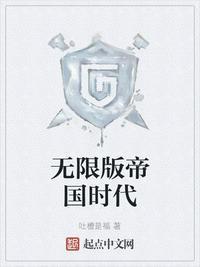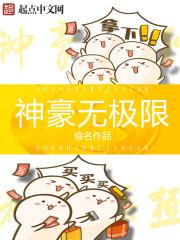笔趣阁>一本反套路的二/战言情文 > Kapitel 16(第2页)
Kapitel 16(第2页)
“但小姐对于文笔确实很有把控力。”季羡林话锋一转,开始明里暗里地试探起我的受教育水平。
我真不明白,一名年轻女性,能写长篇科幻小说,内容涉猎天文、物理、生物、化学、政治……在这个年代,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她文理兼备,至少也应该是中产出身么。
德国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季羡林说想“拜读”我曾经的笔墨,我拒绝了:“我离家漂泊,迄今已有五个月。文人写东西向来都是边写边忘的,杜甫不一定背得过《兵车行》,韦庄也记不下《秦妇吟》,您要叫我回忆半年甚至几年前写的文章,实在有点为难。”
开玩笑,我上高中的时候写应试作文,上了大学手机玩得不亦乐乎,一朝穿越,现在又哪里有文字可以给他看?
想到这里,我又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看着对面那欲言又止、犹犹豫豫的神色。既然德国人把季羡林派过来,是一定有任务的。如果他什么也没套出来……也许于我于他都不是一件好事。
“一定要说的话,倒是有二三首小诗还算勉强记得。”
当初选择自己并不擅长的科幻题材,正是因为1930s,这门小众文化局限于英美文学;兴许,德国人见到了我“美国”的一面,还没见到我“中国”的一面,所以不肯完全相信我。既然如此,那么,最能代表中式高等教育的,应当就是诗词这种旧文人的爱好。
我抽出一张稿纸,略一思索,按照我给自己编造的假身世,提笔写道:
缅因猫赞
“我十一岁的时候,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是一只非常蓬松、威武、黏人的北美缅因猫。我的第一首诗,就是为她而写的。”
金瞳凝夜火,蓬尾扫流霞。
扑雀惊丛雪,巡檐踏落花。
鼾雷惊午梦,爪印篆书沙。
莫羡虬龙傲,雍容自一家。
十一二岁的少女,天真浪漫、养尊处优。写诗自然精雕细琢、力求华美,所以是“金瞳”、“流霞”;她以为自己人生无限好,前途正光明,连翱翔九天的龙也不羡慕,只是自矜孤傲地“雍容自一家”。
季羡林不研究古诗文。但他看到我递过去的纸时,还是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惊艳的神色。我知道自己写对了,信心大增,又拿起钢笔:
梦觉
蝶径随云展,芳茵没履深。
觉来方寸地,万镒不抵春。
随着年岁的增长,她应该逐渐发现自己只不过是笼子里的一只金丝雀。虽然住的是豪宅吃的是美食,但没有自由也见不着阳光,只能在梦里想象自己能够在草地上无拘无束地奔跑,沉醉于鲜花与蝴蝶。可是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睁开眼对着重重落锁的卧室,她只能独自叹息,纵有千金又如何?也不过是“万镒不抵春”。
为了凸显多样性,第三首,我填了一阙鹧鸪天。
自诘
赋就璇玑枉费才,天公何苦种愁胎
时该阁绣描眉婢,胜作桐焦爨下材
鹏峻壑,雀金台,九霄鸾啸困蒿莱
而今休说秦贞素,不若菱花数鬓钗
她成年了。她越来越聪明,但也越来越绝望,她已经看透了命运施加给自己的天赋绝非是礼物,而是无穷无尽的折磨,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是让她做无休止被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是让她做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她举世无双,她天纵奇才,那又能怎样?她是什么身份,又能肖想什么。登不上画麟阁,也没人为她绘美人图——还是“休说”吧。与其做烧焦的琴材,不如继续当自己的金丝雀。好歹那些珍馐美味、绫罗绸缎,都是能真真切切享受的,还能够奢求什么呢?自己问自己,也只能自己答自己,除了自我安慰,什么也做不到。
这三首里唯有最后一首最重要。这是写给德国人看的,告诉他们我已经认命了。
然而,季羡林却在看到这一篇时,表现出来了一丝不悦的情绪。
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