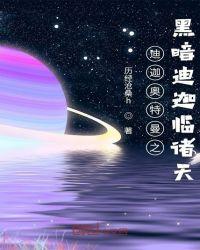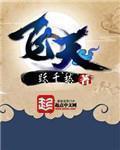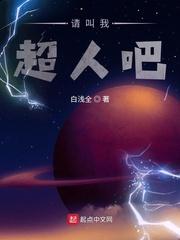笔趣阁>被朝臣听到心声后 > 4050(第6页)
4050(第6页)
赵嘉陵耐心听谢兰藻说完,她点头道:“朕知道了。”一会儿,又说,“一些技艺非皇室珍藏,唯有教给百姓才能带来朕与卿心目中的太平盛世。明德书院虽然没建好,但扬名不用挑时候。到时候用明德书院明道院的名义向民间普及知识好了。”
听到了“太平盛世”四字,谢兰藻动容,她肃声道:“陛下圣明。”
“朕以前年少不像样。”赵嘉陵直勾勾地凝视着谢兰藻,动情道,“朕现在明白了,你的理想亦是朕的,朕想与你一道创造一段君臣佳话。”
换作另外一个被君恩眷顾的人大概会感动得一塌糊涂,谢兰藻只是心念微动。她轻笑一声,道:“敢问陛下,臣的理想是什么呢?”
赵嘉陵一噎,饱满的情绪像是开闸的洪水猛然流泻。
【她怎么回事啊!这合理吗?她不应该说“臣与陛下共赴吗”?】赵嘉陵心中的小人气得跳脚。
可恶,她还得维持着天子的颜面呢。
赵嘉陵喃了喃唇,眼神中多了几分“杀气”:“继宣启之政,开太平之风,为后世之表。”
谢兰藻听着赵嘉陵活泼的心声,没有半点意外之色,她唇角勾了勾,面上浮现了浅浅的笑。
赵嘉陵又说:“朕现在是不是开始懂你了?你还会跟幼时那样嫌弃朕麻烦吗?”
谢兰藻不动声色:“臣不曾嫌过陛下。”
【还当朕三岁小孩那样好骗呢。】
赵嘉陵撇了撇嘴:“口说无凭。”
谢兰藻微微一挑眉:“难道陛下要臣立下字据,陛下再来加盖宝印?”
赵嘉陵:【也不是不行。】
可她脸上装模作样的:“朕十九了,已经不是幼稚小孩。”
谢兰藻意味深长地望了赵嘉陵一眼:“嗯,陛下说得是。”
赵嘉陵:“!”
【她瞧不起朕!】
在赵嘉陵和谢兰藻商议如何从勋贵们的口袋中掏钱时,勋贵们也在考虑类似的事。
火。药、火器应当属于兵学吧?明德书院有这一科目,那教不教啊?就算不教也不打紧,浪头如此凶猛,不跑在前头不行啊!听说明德书院一个班就召四十个人,而且不限出身、不限地域甚至不限年龄,那长安百万人,还有可能轮到自家不成器的孩子吗?
这下好了,不是他们愿不愿意让小孩进入明德书院学习的事儿了,而是能不能排上他们的问题。
怎么办呢?依照勋贵们惯来的行事准则,那当然是猛猛砸钱了!明德书院要建,还得建得极好。
衡山王府中。
王妃李湘掩着唇轻轻咳嗽,她的面色惨怛,毫无血色。
长乐县主赵丹霄在一旁耐心地侍奉。
“既然是改制,陛下必定不允旁人用钱买名额入学,不然跟国子监的乱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李湘柔声道。
长乐县主踌躇片刻,低声说:“儿觉得和妹妹一道在国子监也挺好的。”她们的身份注定了要被陛下冷待,行事也不得张扬。安阳尚且有谢中书顾念旧情庇护着,但昔日东宫的旧人……不提也罢。
李湘缓缓道:“陛下推明德书院,恰需要有人来支持。不要你们如何拔尖,至少要表个态度。陛下若不许,便不强求入学;陛下若是允了,也不必推拒这个机会。”她在府中,虽然大部分人碍于旧事,不与她往来。不过也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态度并不因她的起落而有所更易,故而也能知道些外头的事。
沉默一瞬,李湘看着长乐道:“辛苦你了。”若非家中发生剧变,何以至此?太子被废后,全家都受了牵连,后来陛下追封,才又恢复宗室属籍。她一直劝两个女儿小心谨慎,却压抑了心情,小些的永乐,胆子变得非常小,也没寻常人家的小孩活泼。“你们还是孩子,有时候放纵些无妨。”李湘心中一软,又道。
永乐一脸懵懂,长乐摇头道:“儿不想让家人难做。”
第44章
贵戚们虽然起了“买位置”的念头,但真正实施还得看时候。
赵嘉陵那头动作就利索多了,跟谢兰藻商议后,翌日便在朝堂上提起建工厂的事。一听到“钱”,户部和太府简直是横眉冷目,而谏官们呢,也在这时候凑个热闹,非要说甚么“劳民伤财”。不管遇到什么,谏官们都要说上两句,好像不这么做就不能体现他们的“清骨”一样。
赵嘉陵烦了这些目光短浅的人,视线在底下转一圈,落到谢兰藻的身上,那是怎么看怎么满意。
谢卿何止是好颜色啊!
不过赵嘉陵也不是非要国库出钱,只不过给他们打个底,暗示暗示“朕缺钱”了。
几日后,赵嘉陵便将宫人抄好的《糖谱》交给了银娥,让她着人去宫外将《糖谱》给卖了。当然,天子开门做生意传出去很难听,就算天子不出面,这内官一露脸,谁都晓得了。所以名义上是明德书院的明道院开始“传道授业”。
消息么,当然是先通过安玉婵送到一些“大商人”的耳中。这帮人能在长安如鱼得水,都是有自己门路的。总不会在圣人缺钱的情况下,还要践行“连吃带拿”原则吧?没眼力见的可活不下去。
明德书院尚未建成,至于“明道院”,用的是桓家府邸。安国公桓启虽然被除爵流放了,桓家人都从安国公府上搬出去,但那桓家旧邸毕竟是太后长成的地方,最后挂在了太后的名下。赵嘉陵缺个地儿,跟太后说一声后便将桓府给借用了。顺便将在宫中温书准备贡举的桓楚襄也打发了出去。一张一弛,当然也能借着此事见见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