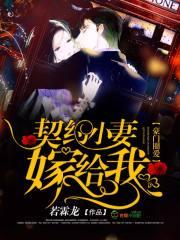笔趣阁>被朝臣听到心声后 > 6070(第7页)
6070(第7页)
来参加常朝的只是官员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呢。借着这个时机,也好排查些“混子”出来。这帮“混子”就别想着致仕了,直接除去官身,回乡躬耕吧。
外邦什么货色,谢兰藻心知肚明。行贿之事,着实常见。像突厥、吐蕃那边大多是为了边市马匹与绢布的交易,而新罗、百济呢,这两国时常打起来,需要大雍的帮助。想要让人说好话,那就只能递钱了。
谢兰藻应诺,又道:“仁宗时,吐蕃吞并吐谷浑,已成我大患。虽有所进取,可大非川与青海之败,使得进取之心尽失。吐蕃虽少进犯凉州,但三朝以来,其势力向西域扩张。先帝时甚至有放弃西域的安西四镇之议。”
赵嘉陵脸色微沉:“朕的准备不是白做的,钱也不是花着看看的。”
“吐蕃赞普登位不久,不会大肆寇边。”沉吟片刻后,谢兰藻又道,“今岁吐蕃入贡之物较往年多些。其余藩国有些许贡使离开长安,唯有吐蕃尽数集聚,恐怕别有打算。”
赵嘉陵眉梢微动:“嗯?”她心中骤然浮现某种猜测,不等谢兰藻开口,便冷声说道,“他们要请婚!”仁宗时吐蕃请婚先是不许,等到打了一场后,双方又握手言和了,只是可怜远嫁的公主客死异乡。在许多人看来,送出一位公主能够平息战火,是不会赔本的买卖。他们扯着一副大义凛然的嘴脸,可什么都没付出,还能在史册上留下慷慨激昂彪炳千秋的洋洋大论,何其荒谬。
“陛下怎么看呢?”谢兰藻问。
“不许。”赵嘉陵不假思索地拒绝,大雍和吐蕃……亲密无间是没有的,但不共戴天可能伸伸手就触碰到了。边境一时的和平难道是和亲换来的吗?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都是虚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落后就要挨打”。想前朝不也与突厥和亲吗?在天下大乱之际,最后突厥骑兵南下,名义上是襄助皇朝,实际上所到之处,放肆劫掠,最后十室九空,生民涂炭,灾难更甚于起义军。
简单的两个字表明坚定的态度,谢兰藻面上浮现笑容。她又道:“贡使在京,还有些时日,陛下不妨让秦国公府接待一二。”
说是秦国公府,其实指的就是李兆慈和火。药,战争毕竟会带来伤亡,酿就无间惨剧,能靠着“震慑”将一切消弭于无形再好不过。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居心叵测,先来欣赏一下大雍的武德。
礼部和鸿胪寺接待外藩的典仪都是歌舞,“恩荣宴”之流排场极大,那金钱也是哗哗如流水,但说实话,这些玩意儿很难发挥炫耀国力、彰显大雍风范的效果。谁能被戏曲震慑住啊,顶多是靠着“奢华”勾起对方的贪婪。
赵嘉陵煞有其事地点头:“先给棒子,再给枣子,朕明白的。”
谢兰藻眉梢微动:“枣子是?”
“他们私底下交易也挣了不少吧?”赵嘉陵心中一盘算,“玻璃、白砂糖能留下他们的全部身家吗?”从西边来的“琉璃”不如大雍产的,那么来往的货物可就得大变了,可以列为与丝绸一样珍惜物,贡使们将它们运回去还是有赚头的。至于他们能不能跟精明的粟特商人拼一拼,那就不关朝廷的事了。
鸿胪寺。
官员们最烦的就是贡使了,吃住上挑三拣四,十分难管束。这帮贡使在宫中还会收敛一二,但在鸿胪寺可就没有半点拘束,一时间各种口音齐飞,而译语人则面色苍白摇摇欲坠。一边是吐蕃贡使要求换更好的住所,一边又是突厥的质问——对方带了一大群马和一万只羊,但很早就已经拒绝了。突厥放弃了羊,但还想着,用一匹马换四十匹缣,然而那些都是羸弱不可用的马!
这个时候,被选为“宣慰使”的李兆慈出现,让鸿胪寺诸臣暗松了一口气。
先前庄子里恐怖的爆炸历历在目,说起秦国公府,朝臣们最先想起来的不是李洽,而是谈笑间弄出天崩地裂效果的李家千金。真神人也!
鸿胪寺的官员自不必说,连吏员都一副大欢喜的模样,任由李兆慈带着自己人全盘接手——只留了鸿胪寺的译语人。如果放在去年年底,吏员们大概不会同意。但现在不一样了。接待藩使固然有油水可捞,然而剩下的是“送行宴”都办过了结果还没出发的藩人,谁还有一双铁手在沸腾的油锅里死命搅和?想要在长安衙门里站稳脚跟,不能给州县那般靠自己的土豪家族做支撑,得有敏锐的直觉。
李兆慈没做过这样的事,但没关系,陛下和宰相说她是精通接待贡使的人,那她就是了,没有人比她更懂外藩事务。于是,怡然自得的李兆慈开始故技重施,准备几日后在庄子里宴请贡使。
贡使们先是惊诧,继而喜出望外。鸿胪寺的官员们很能扯皮打太极,这换上一个小娘子,难不成是大雍的皇帝刻意给他们送好处的?那贡物和回赐的诉求岂不是能轻易达成?
听到贡使们议论的鸿胪寺官吏神色委实精彩至极,这帮桀骜不驯的贡使,等看李兆慈云淡风轻地来上一火铳就能变成老实鹌鹑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凉州的消息传到了长安,奏称吐蕃又派三百人为使,带五千两黄金和珍宝进献,请求许婚。
赵嘉陵一看到奏报脸色就沉了下去,这上一波使者还没回去呢,又增派了三百人过来。要知道之前吐蕃派出将近一千使臣,余下八百分置在甘州、凉州,只许两百人入长安。再让三百新的使臣入境,那甘凉之地,吐蕃之众便过千人。是来朝贡,还是伺机侵边?!
赵嘉陵心中不满:“此辈人面兽心,唯利是图。”
中书舍人道:“不许贡使入境,只是请婚之事,臣以为尚可。宣宗之事,吐蕃已坐大,两战连败,我国兵威不足以攻之,镇之则国力有余,再以和亲为计,备边不深讨为上。”
兵部侍郎大咧咧地说:“吐蕃小丑,屡犯边境。和亲如果有用,仁宗之时何以边患不绝?我军有火器在手,必定所向披靡。”
户部尚书项燕贻瞥了他一眼,也说:“吐蕃国内赞普之争方歇,又有君相失和事,臣以为其人无暇寇边,应蓄养将士,命良将为帅,广收粮储。待我足兵足食,兼之利器在手,可一举取之!”
“和亲之事,日后休提。”赵嘉陵看着中书舍人,眉头微微蹙起。早有预料,也不算失望。这些朝臣都是系统判定的甲等乙等,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着想。这种真诚的短见、陋见,也实在招人心烦。好在未来长成的人不会是这样了,像中书舍人,是一点都没救了,空有拟诏、下笔如流的才思。
得知消息的李兆慈很愿意为君分忧,立马入宫觐见了。她柔和一笑,道:“臣近些时日捕捉到一些奸人,请陛下准许臣借他们的头颅一用。”
赵嘉陵无言。
因议事留在殿中的谢兰藻眼皮子也跳了跳。
这轻描淡写的话语,像是借诗文一览。
说到“奸细”,赵嘉陵她们也知道怎么一回事。能在长安做“奸细”的,大部分都是藩国的人。有的东西明面上是打探不到的,那就暗中来。同样的,大雍也有奸细散落在各处。
说起来,还是工厂给力,研究出来的望远镜,赵嘉陵给火器营配备上了。长安之中,金吾卫明着巡逻,可现在暗处也有眼睛了。本来火器营是不做这些事的,奈何一个个对望远镜兴致极为浓郁。努力也有成果,抓到几个严刑拷打一番,对方就将来历、目的吐得干干净净了。
不过奸细身上是不会有明显证据的,光靠打出来的证词跟藩国撕破脸也没必要,只是暗中记着,并将那些与奸细相关的叛国贼人都处置了。剩下的一些奸细,还没来得及杀。
“若宴会礼仪变更,也知会他们一声,省得他们喧哗起来。”谢兰藻平静道,她克制着自己不去想那鲜血淋漓的场面,视线落到李兆慈那谦和的笑脸上,最后脑子里只剩下一句“人不可貌相”了。
等到李兆慈离开后,赵嘉陵对着谢兰藻感慨道:“慈娘好生生猛,当为女子之表率。”瞥了眼沉默不言的谢兰藻,赵嘉陵又赶忙补上,“当然,在朕心中,唯有你才是第一流人物。”
谢兰藻不至于跟赵嘉陵计较这些,但陛下表达深衷,她也没必要泼冷水。凝眸注视着赵嘉陵,察觉到那显而易见的疲色,她问道:“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