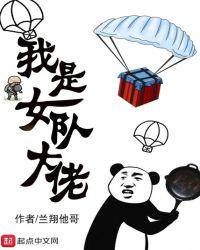笔趣阁>激情年代: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 第四十一章 一九七五(第1页)
第四十一章 一九七五(第1页)
先不说能力,光说江成的威望,他来担任汽车厂的厂长,不管决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都能很顺利的推行下去。
不过让江成物色一批人,来逐渐顶替厂里这一批快要退休的人。江成只能在内心辜负他们的好意了,让他担。。。
雨停后的第七天,山谷里升起一层薄如蝉翼的雾。阳光斜斜地切过树梢,落在纪念馆的玻璃地板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像是谁把一整片星河揉碎了撒在人间。苏岚站在台阶前,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茶,目光落在那三株已经长得齐腰高的水晶兰上。它们的叶片比往年更宽厚,脉络清晰如手写信笺,每一道纹路都仿佛藏着未说出口的话。
她忽然注意到,其中一株花心处浮现出极微弱的波动??不是光,而是一种近乎呼吸的节奏。一吸,一呼,缓慢而坚定,像某个沉睡的人正通过植物的茎脉传递心跳。
“你又来了。”她轻声说。
没有回应,但那株花轻轻晃了一下,露珠滚落,在泥土上砸出一个小小的坑。
自从林远走后,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起初只是收音机偶尔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后来是孩子们在学校画出他们从未见过的脸孔,再后来,村里的老人开始梦见七个人影站在田埂边,不说话,只是静静望着村子的方向。有人说那是魂灵归来,有人说是集体幻觉,只有苏岚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延续??一种超越生死、语言与时间的存在方式。
她蹲下身,指尖轻轻触碰花瓣。刹那间,一股暖流顺着指腹窜上手臂,脑海中闪过一幅画面:一间昏暗的实验室,墙上挂着老式挂钟,秒针停在11:57。七个女人围坐在圆桌旁,彼此握着手,闭着眼,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解脱的平静。周明璃坐在正中央,嘴角微微扬起,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告别。
然后,声音来了。
不是从耳朵听见的,而是直接出现在意识深处,如同童年时母亲哼唱的摇篮曲,温柔却无法抗拒。
>【我们还在等一个人。】
苏岚猛地收回手,喘了一口气。茶杯差点打翻,她稳住手腕,心跳剧烈得几乎要撞出胸膛。
“谁?”她对着花问,“你们在等谁?”
花不动,雾也不动。
但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当天傍晚,她翻出了林远生前最后整理的手稿。那些纸张泛黄卷边,字迹潦草,夹杂着大量涂改和符号标记,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独白。她在第三十七页找到了一段被红笔圈起来的文字:
>“共感网的本质从来不是控制情绪,而是保存‘真实’。当社会开始修剪痛苦、包装悲伤、美化孤独,真正的情感反而成了禁忌。我们建造这个系统,并非为了统一思想,而是为了让那些被遗忘的情绪,有地方可以安放。
>可惜,后来它被改造成了疏导工具。快乐要放大,愤怒要化解,眼泪要引导成正能量。于是,人们渐渐忘了??有些感受,本就不该被解决。
>我常想,如果当初不是被迫关闭系统,而是让它自然演化……会不会,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与痛共处?
>或许,现在还不晚。”
下面是一行小字,墨迹已淡,但仍可辨认:
>“第七个锚点尚未激活。她还在外面。”
苏岚盯着那句话,久久不能移开视线。
第七个。
七位实验体中,六人的名字早已化作水晶兰的记忆载体,唯有最后一个??许沉香??始终未曾显形。她的脑波信号从未消失,但也从未与其他六人同步。档案记录显示,她在系统关闭前三十六小时独自离开基地,去向不明。军方搜寻三个月无果,最终以“失踪”结案。
可林远一直相信,她没死。
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沉香是最清醒的一个。她早就看穿了一切。她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摆脱情感,而是拥有选择沉默的权利。”
苏岚合上手稿,望向窗外。
夜色渐浓,山坡上的水晶兰次第亮起,光芒由蓝转金,又由金转琥珀,像是在经历一场无声的情绪潮汐。她忽然想起昨天村里发生的事:小学五年级的女孩李小满,在课堂上突然哭了起来。老师问她怎么了,她摇头不说。同学们围过来安慰,她也只是低着头,任泪水滑落。整整二十分钟,她就这样坐着,哭得不出声,也不接受任何劝解。
放学后,她走到纪念馆前,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塞进留言箱。值班员后来打开看,上面只写着一句话:
>“妈妈走的时候,没人让我好好哭一次。”
那天夜里,纪念馆外的水晶兰开了一朵从未见过的深紫色花,花瓣边缘泛着银光,宛如凝固的泪痕。
苏岚站起身,披上外套,拿起手电筒走出门。
她要去找那个箱子??林远藏在断链学校地下室的“记忆容器”。那是用观星者4。0的核心残片制成的量子存储装置,理论上能承载人类意识片段的残影。林远曾说,只有当第七个名字回归时,才能真正启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