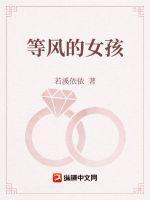笔趣阁>你听懂我吗 > 第 43 章(第1页)
第 43 章(第1页)
两道影子当中隔着一地的尘灰,荒瘪的草地遭一双玛丽珍皮鞋碾过,程筝叮铃着自己的皮箱向他那处走,支着两道眼皮儿,奇怪道:“才多久不见,鹤少爷认不得我了么?”
周怀鹤慢慢地垂下胳膊,一眼也不想要看她,只管自己扭过头向衖堂深处走去。
程筝一径追着,那点抖索的响声便在周怀鹤耳边响个没完,她似乎不大明白他古怪的脸色,又好像是明白的,踩着他的影子问:“你还生我的气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留给我?”
铁墙似的单薄的影子俄而便停住了脚,那熟悉的乌色的眼珠斜着向她一睇,鹤少爷终于是乐意开口:“你又要说你并非故意么?”
“我——”程筝挤出干巴巴的嗓音,心里又觉着不大好说。
见她结舌,周怀鹤调转身子向她,沉默如灰的、带着星点幽怨的眼光缓缓降至她的脸孔上头,掀开病白的两瓣唇:“并非故意偷看我抽屉的信、也并非有意喊警察署的人来捉我?”
“程筝。”他微微咬住白牙,几近是怨恨地唤她的全名,“你拿那样好听的话诓骗我,只为着害死我,如今再来卖个笑脸,告诉我你并非故意,我便活像你瓮里的鳖,供你戏耍、盘玩么?”
默默垂下眼帘,程筝将皮匣子的提手捏得紧了些。
再见面,于周怀鹤来说也许不过半月时间,于程筝来说却还有现代那一遭。兴许在她的那一环时间里,周怀鹤对她太过无怨无悔,以至于程筝差点无法适应他用这样一副冷漠的声口同她说话,尽管她知道他的气恼也不无缘由。
缄默的眼神、苍白失活的面庞,明明是同一个人。
“这事是我做得很欠妥。”程筝哑声道,“可是,难道不容我道歉么?”
他一声不响,单是垂眼钉住她,手指蜷动一瞬,掉过头去继续向前走。
程筝懊恼地闭一瞬的眼,死乞白赖继续跟着他回到厂里去。
尽管周怀鹤对她颇有怨气,可到底是自己那时犯冲,又能如何说道呢?总不能真将人丢在东北,让他不明不白地死掉罢?程筝还没能够摸清这续命之中的规则,而如今是最后一次回溯,行将踏错一步便再无重来的机会了。
亦步亦趋地跟走了不多久,程筝抬眼向他望去。鹤少爷还是鹤少爷,与后来那个说话结结巴巴,满身血地靠在她床头为她点燃回香炉的周怀鹤,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起码是在脾性上,鹤少爷的根骨还是硬。
难哄。
她在心底叹口气,努力调动神经,希图拉回一些好感。
未及思虑出一个好法子,二人便到了那新搭起的钢铁工厂。厂房外是蓝皮铁壳,一个颇简陋的房屋,里头断续发出呜呜如野兽嚎鸣的响声,乌漆色的机器蜷窝其中,也像蛰伏的兽。
硕大的熔炉、蒸起的黑云,将整个场地围困包裹,周怀鹤拉开对过一扇松散的木板门,程筝在他闭门之前赶去,低头向那锁孔看了一看,也是新换的。
里头是一整片的黢黑,程筝立在那门框里向里探望,深感寒凉,仿佛是由空心的砖头搭的临时住所,墙面也并未粉过,一块块砖头垒起,只有西面开了一扇侧窗,恐怕是只能照见早晨的太阳,晌午过后便得点起油灯挂在钉头上。
靠墙两架床,应该能是有人同住。中间砌着炕几,预防过冬,下面挖洞烧炭。这光景较之周公馆里的下人都仿佛还要惨许多,程筝一时说不出话,只听闻那漆黑里擦起一点火光。
屋里电线都没接,周怀鹤擦火柴点了盏灯,橙红色的光蒙上他的脸,他的喉咙似乎始终不见好,在那里闷闷地咳嗽,一张墙灰似的脸咳得泛红。
“我道你是专来看我的下场。”周怀鹤旋即将油灯磕在桌面上,面上却仿佛不显脾性,端着一张好脸,“看罢便回公馆去。”
想他的病也总需要许多的名贵药材温养的,在富丽堂皇的周公馆还供养得,如今落进这敝野遭人囚困着,凤凰落进土堆也是山鸡,更要惹一身的病。
程筝踏进屋里来,将自己捎来的行李轻轻放下,说道:“我是同良少爷一道来的,他准会想办法叫这些人放你,届时你同我一齐回天津去,我当真没有什么坏心思,就是为着这事。”
门吱吱呀呀响得宛如老人喉咙的嘶鸣,周怀鹤眼也不抬,随意拽过一份合同工的文件,在那里仿佛很用心地看,赶人:“你怕是攀不上别的枝子,便又想到我,如今看罢我的笑话,便可以回去报告了。”
“你总将我想得心坏,即便我犯了错,难道就不准我改正么?”程筝道,“再者说,那时假使不是我突然晕倒,不是也得被你说成情。妇,然后跟你一齐被打成捆送来这里么?我以为你我二人是谁也没放过谁。”
周怀鹤突地蹙眉,把着桌子边沿,黑色马褂的领口勒着他汩汩的喉咙:“要是我不放过你,像你害我一般害了你便是,何至于撒谎将你要来沈阳?你以为我——”
枪子儿般接连发射的话语瞬间静止,两双眼睛一高一低地对望,周怀鹤紧抿淡色的唇,偏开眼羸弱地咳嗽,仿佛余下的话是遭突生的咳嗽堵了回去。
程筝静静端望着他蒙上火光的脸。
“以为你什么?”她问个不停,周怀鹤深觉头痛。
“你回去罢,我不想再见你。”他起身,程筝移步拦在他的眼前,周怀鹤避都不能够避开,只得再看向她的脸,呼吸似乎都是静的,但是听着她耍赖道:
“我回不去了。”程筝撩眼皮探他的表情,又移开,仿佛有些难开口:“五爷要纳我,我逃过来了。”
周怀鹤顷刻间冷下眼光,眼尾仿佛气出一抹红,手掌搭在她白色骑马服的肩膀处,很是用力地紧抓:“你就是同我来说这个?”
手腕很用了几分气力,他推开她,“明明是自己不愿意嫁人才逃来了,刚才却说得好像是专为我而来的,我到底就不该信你的连篇的鬼话。”
程筝歪煞脑袋,无奈道:“我没有哄人。”
信用被她自个儿败坏完了,如今周怀鹤是难再信她。
周怀鹤绕开她向外走,那唯二透光的门口,吱呀作响的门俄而被一双飞来的手握停,徐林满身汗涔涔的,两道文青似的山羊须在那里晃,一张长马脸,眼皮一抬先向周怀鹤身后的程筝看,却也来不及扮怪,急口便道:“何工的指头遭机器绞断了,正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