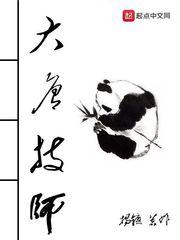笔趣阁>京阙雪 > 满芳沼(第1页)
满芳沼(第1页)
陶青筠忽然道:“糊涂啊糊涂,你们难道忘了我们少时的约定不成?”他清明的眸一扫在场的四人,清了清嗓子,道:“无论是谁害我,你们也不能害我。无论是谁弃我,你们也不能弃我。无论是谁唾我,你们也不能唾我!”
“什么我相信,我不相信,难道这些还不够?日子还得过,天也塌不下来,我们还安安稳稳的活着,朝前看!”他一收折扇,再“狠狠”地敲了秦惟熙与姜元馥的头顶,再让褚夜宁与姜元珺二人,一人挨了一记“重”拳。
姜元珺默不作声,而褚夜宁面上则满是风轻云淡。
秦惟熙看向姜元珺,忽而道:“五哥,昔年先皇一统中原前,前朝那位庸帝,抱残守缺,百姓民不聊生。官宦人家可以借着人权为商,商人因无商可营选择回乡种地,那庸帝唾弃寒门子弟,科举皆世家当道。直到先皇登得大宝,这一切才悉数作废。家与国从不曾分割,当年你言,百姓子民发自内心的安乐,才是真的安乐。可吃饱穿暖,有屋舍可宿,待朝阳升起,可以今日而过再有一身干劲盼着明日,这也是先皇心之所系。”
“五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亲口对先皇所承。若而今你不记得了,可。。。。。。当年只有六岁的我却记得很是清楚。”
姜元珺瞳孔猛地一收缩,面上满是讶色。
好似回到某一年仲夏,他们去蓬莱游乐,途中下山遇见不知从哪窜出来的狼群,他与夜宁将她护在他二人之间,然后他对着那一身鹅黄襦裙,雪白的面上满是明艳之色的少女道:“七妹妹别怕,我来保护你。”
少女面对狼群,那般危机的场面,却毫无惧色,闻之笑得明媚:“行啊,五哥,等你将来做了皇帝也要保护我们大家伙啊!”
他们两小无猜,知无不言,彼此间什么话都可以明说。
他时年为一国储君,却为稚龄。那般混乱情形下,他并未听出其中的含义,为何一定要做皇帝,这天下的君主。
可而今,他才知道,皇权——至高无上!
可掌握生死,揽于一人之手。
时隔太久,他竟有些忘却了,他也曾怕有一日真的就如尘埃一般,他再也抓不住、记不得。
东宫里,那众多的画卷里,暗藏的画像,玉兰花树下,站在秋千架上眺望坤宁宫的姑娘。
他曾问她为何总是眺望坤宁,倘若她愿意,他日成年,他也愿意。。。。。。
然而她对他说:“那里有赵祖母在,皇家深似海,万重门内,心如海底针。我心安处即是坤宁。”
姜元珺盯着她手中那盏茶,蓦地,他想起了罗家小星初回京城时候在小蓬莱上几人再次重逢,陶青筠的一句笑言:“看看,还和小时候一样贪凉。”
因幼年的小熙最爱吃凉食。夏日阵了西瓜、荔枝与甜桃、凉茶。为此阿烁兄长总是像个教书老先生板着脸给她换掉那一盏盏凉茶。
“你?”他回神。然而,面前的姑娘眉眼间尽是与长兄罗聆相仿的模样。
天色渐暗,已待黄昏。
褚夜宁饮尽瓷壶中最后一盏茶,起身道:“时辰不早了。”
“四哥?”姜元馥喊他。
他垂着眸,忽而冷冷一笑:“可我身后还有褚氏万余将士的英魂,甚至有些连尸首都寻不回故土。”
秦惟熙闻之眼睫一颤。
陶青筠的目光也跟着一闪,姜元馥欲再言,褚夜宁忽然截住了话头,问身侧人:“早间你同谁一块儿来的?既然你哥哥不在,正巧顺路,我送你回去?”
他垂着眼帘,话语却不再似方才那般的沉重。
秦惟熙抬起头看他。
他是在对她说。
而那双,微微笑起来,看都谁尽现神情的一双桃花眼此刻正看着她。身覆一身鸽血红长衫,金冠高束,身姿如青松挺拔,负着手半弯着腰,挑眉问:“走?”
似在哄骗邻家小儿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