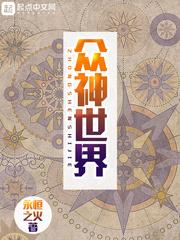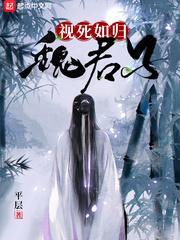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二百七十六章 放榜(第1页)
第二百七十六章 放榜(第1页)
“确实。”众幕僚都读过杨慎的院试文章,皆认为白胡子说得没错。
萧提学却淡淡道:“我问过用修,他说相信仅凭第一篇文章就足以脱颖而出了,所以在写第二篇时没有太用心。”
“唉,不该大意啊。这么重。。。
苏录归家之后,未曾片刻安歇。解元之名虽已传遍顺天府,然他深知,此不过科举之路初登台阶,前路险?,尤胜于今。乡试既毕,会试在即,京师风云变幻,非一介书生所能尽察。而张家之恨意,早已如毒蛇盘踞,只待时机噬人。
夜半,苏录独坐书斋,窗外月色清冷,照得案上试卷泛出微光。他正反复推敲《春秋》大义中“尊王攘夷”一题的答法,忽闻院外脚步声急促,似有人奔来。未及起身,门扉轻叩三下。
“公子,是我。”是苏福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几分惊惶。
苏录开门,见老仆衣襟沾露,面色苍白。“何事如此慌张?”
苏福四顾确认无人,方低声说道:“方才我在城南茶馆听几个吏员闲谈,说……说太师府已遣心腹赴礼部打点,暗中递话,称本届会试主考须‘慎选寒门’,尤其要防‘妄议祖制者’入榜。他们还提到了您??说那篇‘改漕为折’的策论,实乃动摇国本,若放其进士及第,恐开风气之恶端。”
苏录闻言,指尖微微一颤,随即镇定下来,轻轻点头:“原来如此。”
他早知自己文章锋芒太露,必招忌惮。然他亦明白,若为求稳妥便藏锋匿锐,宁可不试。父亲一生刚直,终被排挤贬官,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宁为真言受戮,不作谀词偷荣。”此语如刻骨铭心,岂敢忘怀?
次日清晨,一封密信由一位陌生驿卒送来,封口盖有户部旧印。苏录拆启细读,竟是当年父亲同僚、现任户部右侍郎李维桢所寄。信中写道:
>“贤侄才识卓绝,文不负父志,令人欣慰。然朝中权柄倾轧,新政旧法之争愈烈,阁老分党,宦官掣肘,非单凭才学可通达也。汝策论所言‘折银代粮’,实与当今首辅欲行之‘一条鞭法’暗合,然彼辈忌讳直言者夺其先声,恐借题发挥,反斥汝剽窃机务、沽名钓誉。望慎言谨行,韬光养晦,待时而动。若愿来京,可居我宅西偏院,暂避耳目。”
苏录读罢良久无言。他知道,这不仅是警告,更是一条隐秘之路??一条通往权力核心边缘的小径,却布满荆棘。
半月后,苏录辞别母亲,携考篮再度启程赴京。临行前夜,母亲默默为他缝补冬衣,针线穿引之间,泪落无声。苏录跪地捧手:“娘亲放心,儿此去非仅为功名,更为洗刷父亲冤屈,争一口公道之气。”
老人抬手抚其额,声音颤抖:“你爹走时,连块像样的墓碑都不敢立。如今你能站在万人之上,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记住,活得长,比站得高更重要。”
马车辚辚驶出城门,秋风卷起黄沙,遮天蔽日。京城已在百里之外,而命运的棋局,正悄然落子。
抵达京师当日,天降细雨。长安街两旁朱门深锁,檐角飞翘如鹰隼俯视众生。苏录依信投奔李侍郎府邸,果有一处僻静小院相待。李维桢亲自接见,年逾六旬,眉宇间仍有英锐之气。他细细询问苏录乡试作答经过,听到“道并行而不相悖”一句时,竟起身踱步良久,终叹曰:“令尊当年在户部议事,亦常说‘治国如调琴,弦太紧则断,太松则废’。你们父子,魂魄相通啊。”
当晚,李府书房灯火未熄。李维桢取出一册蓝布包裹的奏稿副本,递给苏录:“这是你父亲万历二十三年所上《漕运十弊疏》,原档已被销毁,唯我私藏一份。你文中所引,十之七八皆出于此。明日我会将此件呈交内阁大学士周延儒,他是少数尚存公心之人,或可在会试前为你稍作周旋。”
苏录双手接过,触纸如触父骨,热泪几欲夺眶而出。
然而,风声终究泄露。
三日后,宫中传出消息:原定主持会试的礼部尚书陈?突染重疾,请辞监试;改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太师张廷弼门生刘景明代为主考。朝野哗然??刘景明素以“守经泥古”著称,曾公开抨击“一条鞭法”为“乱政之始”,更在讲筵中斥责年轻官员“好为新奇之论,惑乱圣听”。
显然,这是张廷弼一手安排。
与此同时,京中各大书院忽然流传一则谣言:顺天解元苏录,其乡试策论实为其师代笔,更有传言称他曾贿赂贡院书吏,提前窥题。虽无实据,然流言如蚁附膻,渐成气候。
苏录闭门不出,日夜研读《周礼》《通典》,并重新梳理父亲遗留笔记,试图从中找出更多可用于会试的真知灼见。他明白,在这场博弈中,唯有以无可辩驳的文章压倒一切质疑。
会试前三日,李维桢悄然带来一个消息:“周大学士已阅你父亲遗疏,并批注八字:‘忠鲠可悯,其子当惜。’他答应在阅卷时留意你的卷子,若确有大才,愿力保一二。”
苏录伏地再拜,感激涕零。
终于,春闱开考。
贡院大门开启那一日,京华烟雨迷蒙。数千举子鱼贯而入,号舍之间人影幢幢,笔墨??之声不绝于耳。苏录仍被分至南区,却是第三排,较上次略宽。他铺开考篮,取出笔砚,心中默念父亲遗训。
首场试题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