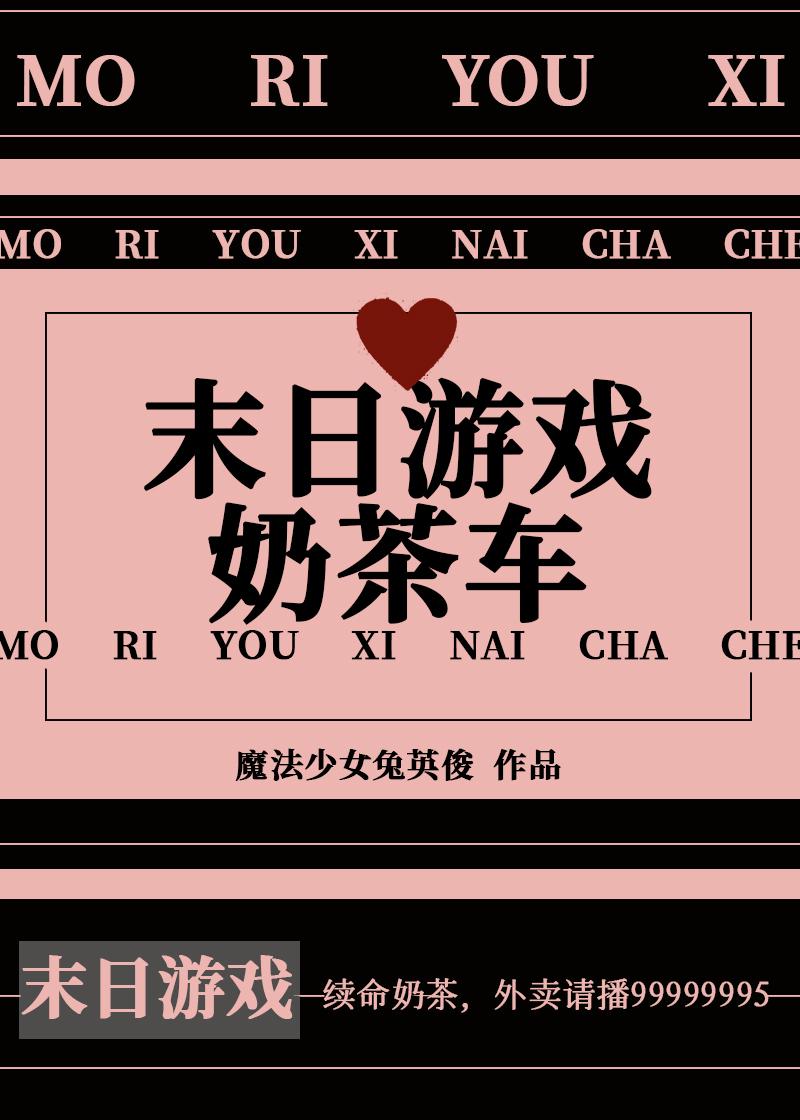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二百七十六章 放榜(第3页)
第二百七十六章 放榜(第3页)
李维桢见牌色变:“东厂插手科举,前所未有!此乃张廷弼勾结内宦之举,意在构陷你舞弊或通敌!”
苏录冷笑:“他们越是如此,越说明惧我。”
第三日清晨,殿试开考。
紫禁城太和殿前,三百贡士肃立等候。金銮殿内,龙椅之上,万历帝年迈体衰,然目光如炬。司礼太监宣读策题:
**“昔汉武外攘匈奴,耗尽天下;唐宗和亲突厥,示以柔仁。今北虏屡犯蓟辽,杀掠百姓,兵部主战,户部忧费,卿等以为,当以何策御之?”**
众人心头一沉。此题表面问边防,实则考治国权衡??战与和、军与财、刚与柔,牵一发而动全身。
苏录执笔沉思良久,终落第一字。
>“臣闻: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御虏之道,不在一战之胜负,而在长久之势衡……”
他提出“三策并举”:
其一,整顿边军,裁汰老弱,重用将才,实行“屯田养兵”,减轻中央负担;
其二,开放边境互市,以丝绸茶叶换马匹牛羊,既缓冲突,又富边民;
其三,派遣儒臣赴蒙古诸部讲学,传播礼义,渐化其俗,“以文化夷,胜于十万雄师”。
最后,他写道:
>“夫王者之师,止戈为武。然止戈者,非怯也,乃智也。能战而后能和,能和而后能久。今我朝兵力未衰,财力尚足,正当以威立信,以信怀远。若一味主战,则劳民伤财;若专事和亲,则损威失体。唯执两用中,刚柔相济,方可建万世之安。”
全文洋洋洒洒三千余言,条理清晰,见解深远,尤以“以文化夷”一语震动朝堂。
阅卷官连夜评定,争议激烈。有大臣斥其“书生空谈”,亦有阁老赞其“经纬之才”。最终,主考官刘景明虽不满其革新之论,然不得不承认:“此卷见识超群,文气贯通,实为本届第一。”
天子亲览三甲卷,读至苏录策论末段,久久不语,忽拍案而起:“此子之言,深得朕心!昔朕少年时亦思此道,惜无人敢言。今得此人,国家之幸也!”
遂御笔亲点:
**“第一甲第一名:苏录。”**
圣旨下达那一刻,整个京城为之震动。
状元郎三字,响彻街巷。
而张府之中,张廷弼摔碎整套青瓷茶具,咬牙切齿:“今日你夺我孙前程,他日我要你九族陪葬!”
苏录披红挂彩,骑马游街,万人空巷。百姓争睹新科状元风采,有老妇焚香祷告:“苏家忠魂有知,今日总算扬眉吐气了。”
他立于高台之上,望着巍峨宫阙,心中无喜无悲,唯有一念清明:
这一纸功名,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父亲的冤屈尚未昭雪,新政之路荆棘遍布,而权力的深渊,已在前方张开巨口。
但他知道,只要持心守正,纵千军万马,亦不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