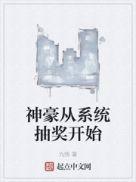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二百七十八章 质疑贾卢理解贾卢成为贾卢(第1页)
第二百七十八章 质疑贾卢理解贾卢成为贾卢(第1页)
“呵呵,拿来本院瞧瞧,到底什么样的文章,能让云鉴先生激动成这样?”萧提学饶有兴致地笑道,心中却颇不以为然,觉得老先生太夸张了。
他如今虽然博通五经,但当年科举时,治的便是《礼记》,也是凭此才考上。。。
夜阑人静,烛火摇曳。苏录伏案于书斋之中,笔走龙蛇,墨香氤氲。窗外秋风扫过庭院梧桐,落叶簌簌,如诉如吟。他额角微汗,指尖却稳如磐石,一纸策论已近尾声。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赋役之重,征敛无度,百姓疲于奔命,田亩荒芜,仓廪空虚……非良政也。”他低声念着最后一句,提笔顿了半晌,终是落下一个遒劲有力的“矣”字。
搁笔长舒一口气,苏录仰靠椅背,双目微闭。连日来推演乡试题目,昼夜不息,脑中千头万绪如江河奔涌,此刻才稍得安宁。桌上堆满誊抄整齐的八股习作、策论草稿,还有几页未完成的经义辩解。这些都是为两个月后的应天府乡试所备,容不得半点疏忽。
门外传来轻叩之声。
“公子,药煎好了。”是小厮阿福的声音,低而恭敬。
“进来吧。”
门开一线,阿福端着青瓷碗缓步而入,脚下放轻,生怕惊扰了这深夜的寂静。他将药碗放在案边,又悄悄吹了吹热气腾腾的汤汁,才退后两步道:“老夫人说,您这几日熬得太狠,劝您早些歇息。”
苏录睁开眼,笑了笑:“我知道。可时不我待,明年便是会试之期,若连乡试都过不去,谈何金榜题名?”
阿福低头不语。他知道这位主子自幼聪慧过人,七岁能文,十二岁通五经,十三岁便在县试中夺魁。可偏偏家道中落,祖父遭贬谪死后,家中再无靠山。父亲郁郁而终,母亲独撑门户十余载,供他读书。如今他已是十九,若再不能考取功名,一家生计都将难以为继。
“公子,”阿福犹豫片刻,终于开口,“昨日城南张举人家贴出告示,邀本地才子共议‘井田可行否’之题,设宴款待,还许荐于学政大人。您……要不要去?”
苏录闻言皱眉:“张举人?可是那个三年前靠贿通考官才中的举?”
“正是。”
“那就不必去了。”苏录冷笑一声,“此人文章浮华无根,议论皆拾人牙慧,不过仗着家中有钱,结交权贵罢了。我去与他同席论学,岂不是自降身份?再说??”他指了指桌上的策论,“我的学问,不必靠他推荐。”
阿福不敢再多言,只默默收拾药碗退出。
苏录重新披衣起身,走到窗前推开木棂。月光洒落院中,照见那一方小小天井,仿佛一方砚台盛着银水。他凝望着夜空,心中思绪翻腾。
他知道,自己这条路走得艰难。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同年提携,甚至连个像样的书院都进不去。金陵虽为江南文薮之地,但真正能入钟山、紫阳诸院者,非世家子弟即达官之后。他一个寒门孤生,只能靠自学苦读,一步步摸索前行。
但他也有自信。
自十五岁起,他就开始系统研习程朱理学,兼览陆王心学之要旨;对《春秋》三传烂熟于心,尤精《左氏》褒贬笔法;于《周礼》《孟子》亦多有心得。八股一道,更是反复锤炼,务求每一破题、承题皆有来历,每一起讲、入手皆合矩度。
他曾把自己最得意的一篇《君子务本》拿给一位致仕的老翰林看过。那老先生初时漫不经心,待读至“本立而道生,非徒孝悌而已,乃天地生生之机所托也”,忽然拍案而起,连声道:“奇才!此子不出十年,必为天下宗匠!”
可惜那位老先生次年便病逝了,未能引荐于人。
苏录并不怨天尤人。他知道,命运从来不会轻易垂青谁。唯有勤勉不懈,方能在万千士子中脱颖而出。
翌日清晨,天刚蒙亮,苏录便已起身洗漱。用过粥饭后,正欲继续温书,忽听门外喧哗。
“苏兄!苏兄可在?”
声音洪亮,带着几分书生意气。苏录一听便知是谁??李怀瑾,他的同窗好友,也是金陵城中有名的才子。
推门而出,果见李怀瑾一身青衫,手持折扇,笑容满面地站在院中。身后还跟着两人,一个是赵明远,另一个竟是久未露面的周景和。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苏录惊喜不已。
“还能为什么?”李怀瑾大笑着上前挽住他手臂,“乡试在即,咱们几个老友还不聚一聚?况且??”他压低声音,“听说这次主考官极重实务策论,不喜空谈性理。我等正好切磋一番。”
赵明远点头附和:“昨儿我在府学听到消息,本届考官是从户部调来的陈侍郎,此人曾在浙江整顿盐政,一手清查贪弊,震动朝野。他最恨纸上谈兵之辈,若对策中无具体条陈,纵然辞藻华丽,也难入其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