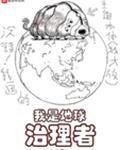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二百八十七章 师伯助你(第2页)
第二百八十七章 师伯助你(第2页)
散会之后,他独自步行归家。
途中经过一座石桥,桥下流水潺潺。忽听得背后有人唤他名字。回头一看,竟是昔日同窗李慎之。此人出身寒门,才华出众,早年与苏录并称“南北双秀”。只因一次廷试失言,得罪权臣,被贬出京,多年未见。
“多年不见,风采更胜往昔。”李慎之笑着上前,眼中却藏着一丝疲惫。
两人并肩而行,聊起旧事。说到动情处,李慎之忽然低声道:“你知道吗?这次会试,有人已经在暗中串联,欲推‘新学’为正统,排斥异己。你若还坚持‘祖宗之法不可轻变’那一套,恐怕难有好果。”
苏录脚步一顿:“谁在牵头?”
“还能是谁?王介甫门下那几位得意弟子罢了。”
苏录眉头微皱。他知道王安石素来主张改革,认为“穷则变,变则通”。但他也清楚,任何变革若脱离实际,操之过急,只会激起民怨,动摇国本。他并不反对新政,只是主张循序渐进,以教化为先。
“我自有分寸。”他平静地说。
李慎之叹了口气:“你总是这样,温吞如水,看似无害,实则固执得可怕。你以为保持中立就能全身而退?在这庙堂之上,没有真正的中间路可走。”
苏录望着远处宫墙,阳光洒在琉璃瓦上,金光耀眼。他轻声道:“我不是想走中间路,我只是不想背离初心。当年我们读书,是为了明道济世,不是为了攀附权势、党同伐异。”
李慎之苦笑:“初心……说得容易。可当你真正站到那个位置上,还会记得什么叫初心吗?”
两人就此别过。
当晚,苏录彻夜未眠。他铺开宣纸,提笔蘸墨,开始草拟对策。针对“民为贵”一题,他决定从三代之治说起,引用《尚书》《左传》等典籍,强调仁政爱民乃立国之本;同时巧妙融入当今时政,既肯定整顿财政之必要,又提醒不可竭泽而渔。
写到一半,笔尖突然一顿。
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完全按自己的理念去写,这篇文章很可能被视为保守派言论,遭到革新派打压。但如果一味迎合潮流,又违背了他做学问的原则。
怎么办?
他起身走到院中。夜风拂面,带来一丝清明。抬头望天,北斗七星清晰可见。他忽然记起小时候塾师说过的一句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啊,文章可以修饰,立场可以伪装,但一个人的良知,终究骗不了自己。
他重新回到书房,撕掉原稿,另起一篇。这一次,他不再回避矛盾,而是直面问题??既承认国家面临困境,必须变革图强;又强调变革必须以人为本,以稳为基。文中援引汉初萧曹治国、唐初房杜辅政之例,说明“守成与创新并非对立,而在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写毕,东方已泛白。
他搁下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这篇文字或许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它真实表达了他此刻的思想。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能坦然面对。
接下来几日,他闭门谢客,专心打磨文章。每日清晨诵读经典,午后练笔,晚间反思所得。家人送来饭菜,常常凉了也不曾动筷。母亲心疼地劝他保重身体,他只笑道:“娘放心,儿自有分寸。”
二月初八,贡院外人山人海。
各地举子穿戴整齐,怀抱文具,排队等待入场。巡查官吏手持名单逐一核对身份,气氛肃穆紧张。苏录站在队列之中,神情平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脚踏黑履,腰束素带,毫无奢华之气,却自有一股沉稳气质。
轮到他时,一名副主考官瞥见他的名字,微微颔首:“苏录?可是婺州那位解元?”
“正是晚生。”
那官员略一打量,点头道:“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不凡。愿君此番蟾宫折桂。”
苏录躬身施礼:“多谢大人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