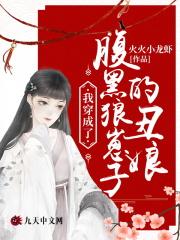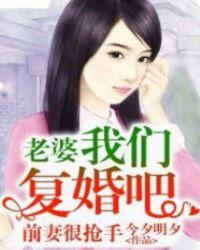笔趣阁>炽年长明 > 集训(第2页)
集训(第2页)
“心里有东西堵着,笔就死了。”周老师的声音不高,带着杭城口音特有的软糯,却像一颗石子投入耿星语沉寂的心湖。
耿星语猛地抬头,嘴唇动了动,想辩解,最终却只是黯然地垂下眼睫:
“老师,我……我感觉不到那股‘气’了。我知道该怎么写,但手不听使唤,写出来的……都是空的。”
周老师放下那张废稿,目光落在她微微颤抖的手上,又移到她那双努力维持平静、却难掩疲惫和迷茫的眼睛。
“耿星语,”他叫她的全名,语气严肃了些,“你以前写字,是为了什么?”
耿星语怔住了。为了什么?小时候是父母的期望,后来是为了静心,是为了在情绪风暴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现在,是为了高考,是为了让妈妈放心。
周老师似乎看穿了她的思绪,轻轻摇了摇头:
“为别人,为目的,都写不好字。”他拿起她桌上那支兼毫笔,在指尖转了转,“笔,是有生命的。它感受执笔人的心跳,呼吸,还有……那份‘真’。”
他指向窗外:
“你看那棵树,经历风雨,有的枝条折断,有的叶子枯黄,但它还在生长,姿态或许不完美,但那就是它真实的生命。你的字,以前有股‘争’气,有不甘,有挣扎,那是你当时的‘真’。现在,”他看着她,目光如古井,深邃而包容,“你的生命状态变了,经历了大风浪,暂时驶入了一片无风带,平静,但也茫然。这,难道就不是一种‘真’了吗?”
耿星语的心被触动了一下,她喃喃道:
“可是……这样的‘真’,太平淡,太无力了……写出来的字,没有力量。”
“谁说的?”周老师拿起她临摹的《兰亭序》,“王羲之写《兰亭》时,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畅快。颜真卿写《祭侄稿》时,是悲愤交加,字字血泪。不同的生命状态,自有不同的力量。静水流深,也是一种力量。”
他铺开一张新纸,递给她:
“别想着非要找回从前那个自己。接受现在的你,接受这份‘温吞’,这份‘空白’。就从这里开始。今天不临帖了,就写你此刻最想写的一个字,随便写,好坏不论。”
耿星语犹豫着接过笔,蘸墨。脑海中纷乱闪过许多字——静、安、忍、病……最终,她深吸一口气,手腕悬停片刻,然后落下。
一个“定”字。
笔画依旧不如从前稳健,结构也略显松散,墨色有些洇开。但奇异的是,当她不再执着于“必须写出力量”,只是诚实地表达此刻内心最深的渴望——“安定”时,笔下那股滞涩感似乎减轻了一些。这个字不完美,甚至有些笨拙,但它不再是一具空壳。
周老师看着这个字,缓缓点头:
“你看,笔活了。虽然还很虚弱,但它开始呼吸了。”
他看着她,眼神带着鼓励,“艺术这条路,尤其是书法,从来不是逃避伤疤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是安放所有生命痕迹的地方,包括你的风暴,你的治疗,你的迷茫,还有你现在这份想要‘定下来’的心。”
“不要把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对立起来。她们都是你。集训还长,高考也并非终点。慢慢来,让笔下的痕迹,跟着你一起重新生长。”
周老师的话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撬开了耿星语心中那块坚冰的一角。她看着纸上那个歪歪扭扭却无比真实的“定”字,眼眶微微发热。
她依旧不确定前路如何,依旧害怕那片记忆的空白和情感的温吞。但此刻,她仿佛看到了一丝微光——
或许,她不需要强迫自己变回从前,她可以学着与这个经历了风暴、正在缓慢修复的、新的自己相处,然后用这双或许不再激烈、但更加坚韧的手,去书写属于“现在”的篇章。
她重新拿起笔,蘸上墨,这一次,感觉手腕似乎沉静了一分。
周老师嘴上不说,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他看着那个靠在窗边的女孩,目光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了然与赞许。
耿星语的状态,确是一日好过一日。并非指她突然变得如何神采飞扬,而是她身上那种紧绷的、试图与什么对抗的劲儿,渐渐松了下来。
她依旧安静,但不再是空洞的安静,而是一种如同深潭水、内里自有暗流与生机的沉静。
她不再执着于每一笔是否完美复刻古帖,也不再焦虑于自己笔下是否还有从前的“争”气。她开始真正地“读”帖,不再是机械临摹,而是去感受颜真卿《祭侄稿》笔墨间的悲愤决绝,去体会苏轼《寒食帖》字里行间的萧瑟与旷达。
她甚至开始尝试将旅途中所见的山川气息、将母亲电话里强装无恙却泄露的一丝疲惫、将自己服药后那种奇异的平静与疏离……所有这些复杂的、属于她此刻生命的滋味,都试着融入笔端。
笔下线条渐渐褪去了最初的僵硬与虚浮,变得沉稳而富有韧性。那份因“空”,不再是她恐惧的敌人,反而成了一种奇特的容器,让她能更纯粹地去接纳和转化古人的精神与自身当下的体验。
她的字,少了些少年人不管不顾的锋芒,却多了一种历经磋磨后、知其艰难仍要向前的静默力量。那是一种将痛苦沉淀后,结晶出的、更为内敛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