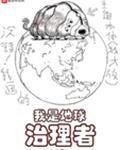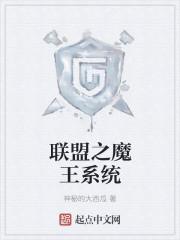笔趣阁>炽年长明 > 泪(第1页)
泪(第1页)
日与夜的泪啊,悄无声息,却又无穷无尽,打湿了枕头。
她终于哭了出来。
从重症监护室那带着消毒水和生命支持仪器冰冷触感的枕头,到转入心理病房后,同样洁白、却似乎承载了更多无声呐喊的枕头。
耿星语不知道在这些不见天日的病房里度过了多少个日夜。时间失去了刻度,变成了监护仪屏幕上跳跃的数字,变成了护士定时送药查房的循环,变成了窗外天色在厚重窗帘缝隙间,那一点微不足道的、从明到暗又从暗到明的交替。
起初在ICU,她的眼泪是生理性的,混杂着洗胃后的苦涩、药物副作用的眩晕,以及身体被强行从死亡线上拉回的剧烈不适。
那时流泪,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如同身体在自行排解某种毒素,浸湿的枕头带着生命最原始的狼狈。
转入心理病房后,环境似乎“温和”了一些,没有了那些冰冷的救命机器,但束缚却更深地嵌入了内心。
眼泪变得沉默,不再是汹涌的浪潮,而是持续的、细密的渗漏。常常是夜深人静时,她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没有任何啜泣的声音,只有温热的液体不断从紧闭的眼角渗出,悄无声息地濡湿一大片枕套,直到那片冰凉在黎明时分变得僵硬。
枕头见证了她所有的脆弱。它吸纳了她的绝望,她的茫然,她对母亲蚀骨的思念,以及对自身存在的深刻怀疑。
有时,她会睁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任由泪水滑落,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也随着这些水分,一点点被抽离,蒸发在这充满药味的空气里。
护士会定期更换枕套,动作轻柔,带着职业性的同情,但她们换不掉那份浸透在记忆纤维里的潮湿与悲伤。
白天,她或许会配合治疗,会按时吃饭吃药,甚至会对着心理医生勉强牵动嘴角。但每当夜晚降临,独自面对那片空白和寂静时,堤坝便会再次溃决。
枕头成了她唯一的、沉默的共谋者,承载着她无法向任何人言说的,那片名为“失去”的、无边无际的、冰冷的海洋。
她就在这日与夜的交替、泪水的浸染中,漂浮着,沉沦着,不知何处是岸,甚至不知,自己是否还想找到那片岸。
时间像渗过沙砾的水,在消毒水气味和周期性情绪评估中,悄无声息地流走了两个月。耿星语依旧住在病房,情绪像一潭不再起波澜的死水,稳定,却也毫无生气。
她按时服药,配合治疗,但眼神里的光似乎被永久地封存进了那个枣红色的木盒里。
这天下午,耿峰再次出现了。与两个月前那次带着表演性质的探视不同,这次他显得更加务实,甚至有些匆忙。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带着从外面带来的、与病房格格不入的风尘气息。
他没有过多寒暄,径直走到耿星语床边,将一份折叠起来的材料放在床头柜上。
“星语,”他的语气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平稳,带着不易察觉的催促,“下周,就是联考了。周老师……就是你杭城那个书法老师,他把报名表和相关的通知都发给我了。”
耿星语靠在床头,目光落在窗外光秃秃的树枝上,没有任何反应,仿佛没听见。
耿峰等了几秒,见她毫无回应,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用一种试图显得语重心长、实则缺乏温度的语气继续说:
“我知道你最近情况不好,但是星语,这个机会不能就这么放弃了。你妈妈……她之前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考上个好大学。你现在休学,如果连联考也不参加,之前所有的努力,还有你妈妈为你付出的……不就都白费了吗?”
他刻意提到了柏岚,试图用这最后的筹码来撬动女儿的意志。
耿星语的睫毛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但依旧没有转头。妈妈期望的……是啊,妈妈期望她好好活着,期望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可现在,“未来”这个词,在她听来空洞得可怕。
耿峰见她还是不说话,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手续方面你不用担心,爸爸会帮你处理好。你只需要表个态,到底还考不考?周老师说,以你之前的水平,就算这两个月没练习,冲一冲也还是有希望的……听说,他之前还很看好你,觉得你是状元的苗子。”
他将“状元”两个字,咬得稍微重了些,仿佛那是一个可以唤醒她斗志的响亮名号。
病房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模糊的城市噪音。
许久,耿星语才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她的目光第一次落在了耿峰脸上,那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波澜,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冰冷的疲惫。
她看着父亲那张写满了功利和算计的脸,看着他西装革履与这病房的苍白形成的鲜明对比,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找不到一丝真正属于父亲的、感同身受的痛楚。
然后,她用一种沙哑的、轻得几乎要散在空气里的声音,清晰地吐出了三个字:
“……不考了。”
没有解释,没有情绪,只是平静的陈述,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