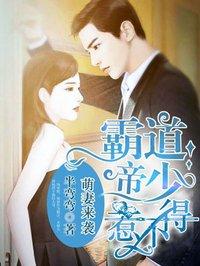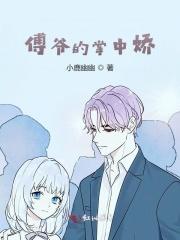笔趣阁>祥子修仙记 > 第198章 嚣张的(第2页)
第198章 嚣张的(第2页)
整整三天三夜,甘霖普降,干裂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村民们跪在泥水中痛哭叩首,不知该谢天,谢地,还是谢那一口被泪水浸透的铜钟。
事后,有人将此事绘成图卷,题曰《万灵共响图》,送往京师。皇帝观后沉默良久,终命史官将其录入国典,列为“仁政感应篇”之首,并加批语:“民声不止于口,亦通于禽兽草木。若使万类皆能言其所苦,则天地亦不忍漠视。”
自此,“听民声”成为治国要务。不仅朝廷设立“采音使”,定期巡行各地收集百姓心声,连边疆戍卒的夜间哨歌也被整理成册,称为《戍音集》,供皇子研读。
而在这片渐渐复苏的土地上,阿音已长成少女。她依旧不能说话,但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用脚踏节、用手划空、用身体摆动来表达节奏与情绪。她在各地开设“无声学堂”,教聋哑之人如何“听见”世界,如何让别人“听见”自己。
一次讲学中,有学生问道:“我们从未听过声音,怎能理解‘归音’?”
阿音蹲下身,将学生的手掌按在自己的胸口。心跳有力,一下一下,撞击着掌心。
她比划道:“你看不见光,但你能感到温暖;你听不见声,但你能感到震动。只要心还在跳,你就活在声音之中。所谓‘归音’,不过是找回那个敢于震动的灵魂。”
话音落处,全场寂静。片刻后,所有人同时用手拍地,用脚跺板,奏出一段没有旋律却充满力量的节奏。那声音汇成洪流,冲出学堂,惊起林中宿鸟。
数日后,邻村一位多年失语的老妪突然开口,喃喃道:“我梦见……一群孩子在跳舞,踩得很用力,像在敲钟……”
徐彬此时已是清音坊主事,年近五旬,两鬓染霜,却精神矍铄。他主持编纂《天下心声录》,收录十年来所有公开忏悔、控诉与告白,不分贵贱,不论是非。有人质疑此举会暴露国家丑陋一面,动摇统治根基。
徐彬只答一句:“疮疤若不敢揭,终将溃烂。唯有直面血肉,方可生肌愈合。”
某夜,他在灯下校对最后一篇??正是当年他自己焚烧冯老庄后的梦中所见。写至“母亲唱起童谣”一句时,笔尖顿住,泪落纸上,晕开墨迹。
次日清晨,他命人将全书副本送往各地书院、寺庙、市集,并在每册扉页印上一行小字:
>“此书中每一个字,都曾是一个人深夜无法入睡的理由。
>愿它们不再孤独。”
十年光阴流转,世间早已不同。曾经森严的“绝音阵”遗址上,如今建起了露天戏台,乡民们唱着俚曲,笑声飞扬;昔日噤声使盘踞的黑塔,变成了儿童音乐学堂,每日传出稚嫩笛声;就连皇宫太和殿前的御道两侧,也增设了两排小型铜铃,供来访使者或平民百姓摇响陈情。
唯有西漠废庙前的碑林,依旧静默伫立。风吹沙移,掩了又露,露了又掩。但每逢月圆之夜,总有旅人声称听见那里传来合唱??男女老少,南腔北调,齐声吟诵那句铭文:
>“伪声可封,真音不灭。
>裂心之处,即是归途。”
有人说,那是亡魂归来。
有人说,那是生者铭记。
也有人说,那是祥子仍在行走,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敲响每一颗尚未麻木的心。
直到某年冬雪,一名游方僧人路过此地,在碑林中央发现一具盘坐的遗骸。衣衫褴褛,仅余右臂完整,指骨微曲,似曾握笔。身旁沙地上,刻着最后一行字,已被风刮得模糊不清,但仍可勉强辨认:
>“我不曾离去。
>我只是变成了你们听见的那一刻。”
僧人合十默哀,欲为其掩埋,却见朝阳初升,金光洒落碑面,刹那间,所有石碑同时轻震,嗡鸣齐作,声浪滚滚西去,穿越沙漠,越过高山,直达天涯尽头。
那一刻,东海渔妇停下摇铃的手,江南学子搁下竹板,北疆牧童停止吹笛,西南猎户放下石器……万人抬头,仿佛冥冥中有谁在呼唤。
他们不知道那是结束。
他们只知道,那是又一次开始。
多年以后,有个孩子问老师:“祥子是谁?”
老师没有回答,而是带他来到村口那口悬挂已久的铜钟前,递给他一根细绳。
“你拉一下试试。”
孩子用力一拽,钟声轰然响起,悠远绵长。
老师微笑:“现在你知道了??祥子,就是让你敢拉这一下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