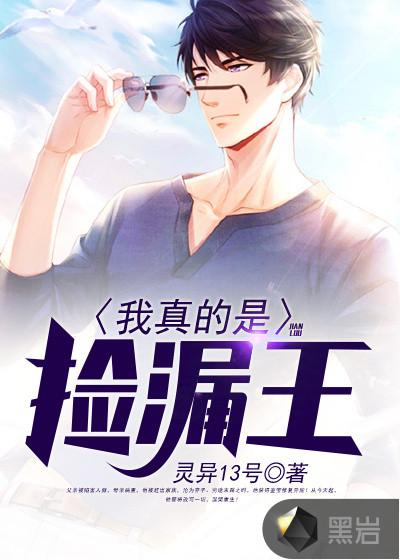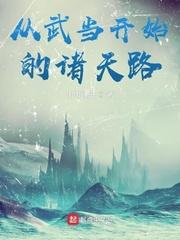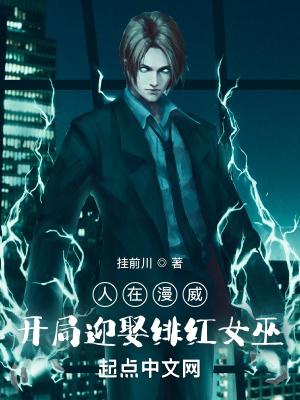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90章 新的温度(第2页)
第90章 新的温度(第2页)
这是他们太熟悉的慢板。无数的名家,都曾在舞台上奏过这一段;几乎每个人心中,都存着一个最爱的版本:或是歌唱般流淌的鲁宾斯坦,或是宁静克制的巴克豪斯,或是光泽细腻的布伦德尔。
可在此刻,江临舟的声音却让他们停住了心中的对照。
他的速度比常见的更微微放缓,却并不拖沓;旋律没有被过度歌唱化,而是带着一种近乎素描般的清晰。他在每个乐句的收尾处,留出一丝极短的呼吸,让旋律仿佛真的在“说话”。而左手伴奏的分解和弦,被他弹得轻而稳,
就像是背景里持久的心跳,不抢前景,却让旋律有了厚度。
这种处理,让人觉得不是在聆听某个大师的诠释,而是在聆听一个少年的心声。熟悉的旋律,忽然有了新的温度。
观众席有人下意识地直起身子。年轻的学生们原本想在心里挑毛病,却渐渐安静下来,目光一点点聚焦在舞台中央。年长的观众则悄然释怀般地笑了笑,心底暗暗感叹:这孩子,竟能把一首被演了无数遍的旋律,弹得如此独
特。
评委席里,有人缓缓放下笔,手指轻敲着桌面,似乎在追随那旋律的呼吸。另一位年长的评委则微微眯起眼,嘴角浮起罕见的笑意。
音乐继续流淌,每一个听过无数次的转折,都被江临舟处理得极为细腻:轻处如低声耳语,厚处则像暗流涌动。熟悉之中生出新意,那是只有在舞台此刻才能捕捉到的声音。
旋律渐渐回到再现。
江临舟的手指轻柔地在高音区拨动,像是小心翼翼地抚平水面的涟漪。左手的分解和弦依旧稳稳支撑,却比开头更轻,仿佛只是在空气里留下最淡的一层呼吸。
熟悉的主题再次出现时,他并没有追求新的变化,而是将声音压得更低,更内敛。音符像从心底深处流出,不再是面向观众的倾诉,而像是独自的低语。
这一瞬间,整个大厅的空气凝固了。
观众们仿佛忘记了自己置身在音乐厅,耳边只有这条纯净的旋律。有人眼眶泛起微光,悄悄低下头;年轻的学生心口一紧,不知为何,竟觉得有点难以呼吸。
评委席上,本已习惯挑剔的几位,此刻也都静默。没有人低头写字,他们只是看着舞台,看着那个在灯光下沉静演奏的少年。
最后几小节,他的触键比羽毛还要轻。踏板极轻地带住,仿佛让旋律悬在空中,既没有完全消散,也没有彻底停顿。
尾声终于落下。
一个极其柔和的和弦,像叹息一般,慢慢融进寂静。
整个音乐厅陷入死一般的静止。没有掌声,没有??,只有心跳在胸口轰鸣。片刻之后,仿佛全场被同一个信号牵引,掌声如潮水般骤然爆发。
那掌声并非因惊艳,而是因触动。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旋律,竟被一个少年弹出了新的形状,新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