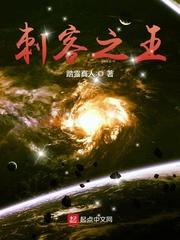笔趣阁>葬明1644 > 第172章 真爱(第3页)
第172章 真爱(第3页)
“这个短锹,以后便叫工兵铲,掘子营内的工兵,要作为标配的作战工具,人手一支,你李铁头要安排出相应的用法,战法和操练之法出来,形成文书之后,报到的中军衙门文书室。”
韩复先是冲着李铁头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复又望向那杜瘸子道:“你将这长短两种铁锹的制式,以及性能,材料,造价等,同样用文书的方式确定下来,形成标准之后,与中军衙门、总工坊以及掘子营三方验收。验收通过之
后,即可大量的打制。”
杜瘸子是戴家昌排挤出去的,现在自己让他来负责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对戴家昌的一种敲打。
但愿这位戴匠头,能够察觉到风向的变化,自觉地做出改变,跟上襄樊营这辆战车前行的速度。
戴家昌是桃叶渡的老人,在自己刚到襄阳的时候,也是为兵马司打制了大量的武器,为兵马司快速成军,击败拜香教,从而在襄阳站稳脚跟,立下过很大功勋的。
韩复是个很感性,很念旧的人,尽管不太喜欢戴家昌这个人,但从情感上来说,他还是不太愿意拿他动刀的。
这个冬天过完之后,韩复要开刀清理的人太多了,他不希望戴家昌这样的桃叶渡老人,也是其中的那一个。
南都宫禁之外,天刚蒙蒙亮,长满了吴宫荒草与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粉味道的南都紫禁城,就在这浓浓的晨雾中若隐若现。
在金陵逗留数日之后,准备回九江的袁继咸,特来陛辞的袁继咸,凝望着这座宏伟庄丽的宫殿,忽然听到有辚辚车马之声传来。
几辆大车穿破雾气,不紧不慢地从宫门内缓缓驶出。
袁继咸恍惚间,仿佛置身于国初全盛之时的宫禁前,仿佛见到了太祖高皇帝的御撵。
那辚辚车马之声越来越清晰,每一次声响,都如同是一道电流,穿越袁继成的全身。
天色晦明不定,高大的宫垣被浓雾笼罩,周围全是白的、灰的、蓝的色彩,远处有并不真切地各种各样的人声。
天气是如此的寒冷,那御撵移动所发出的辚辚之声又是如此的撩动心弦。
袁继咸感觉自己像是在做一场梦,一场无比清醒的梦。
他梦见自己来到了洪武年间,而自己正站在这里,准备迎接那位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的,真正伟大的皇帝。
无愧于“圣天子”这个称呼的,真正伟大皇帝。
这让袁继咸心中如有道道惊雷炸裂,让他不可遏制的浑身颤栗起来。
他弓着腰,完全怀着一种想要匍匐,想要朝圣的心态,紧紧盯着那隐没在晨雾中,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车辆。
那一前一后的两辆大车,终于是刺破了晨雾,完全显现在了袁继成的眼前。
那是两辆用骡子拉着的板车,每一架上都躺着一具僵直的尸体。
袁继咸不知何时直起了身子,张大嘴巴,怔怔地望着板车上衣衫不整的尸体。
就这么怔怔地看着。
直到第二辆近乎一模一样的板车,都快要越过自己以后,他才鬼使神差的快步追了上去,问道:“这两个是何人,因何而死?怎地从宫禁中出来?”
赶车那个太监并不认得眼前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江督袁继成,但见此人官阶不小,分明是方面大员,也就随口说道:“此二女都是旧院的,是马、阮两位大人选进的,昨夜才入的宫,侍奉的皇上。。
负责押车的太监,说话的同时,脸上露出了男人都懂,残缺的男人更懂的笑容。
可惜,先前问话的袁继咸,早已失去了谈话的兴致。
更准确地说,他似乎失去了一切兴致。
心中如有什么东西,片片破碎。
那破碎了的,带有尖锐棱角的东西,又不停地锥刺着他的神经与心脏。
让他整个人都陷入到了极端的痛苦之中。
在与这极端痛苦的对抗里,袁继浑身的精气伴随着出离了身体的灵魂,都远远的飘去。
仿佛可以穿透这层层的迷雾,到达两百七十多年前的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