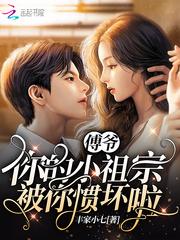笔趣阁>葬明1644 > 第184章 成色(第2页)
第184章 成色(第2页)
原先在众人的想象之中,大顺虽然败了,撤出了关中,但河南毕竟还有明廷的兵马顶着,鞑子一时半会也威胁不到襄阳来。
可如今看情况,河南情势很不乐观,搞不好也要“倡率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了。
这样一来,作为湖广门户的襄阳,就要首当其冲,直面清兵锋芒了。
虽然近一年来,襄樊营在襄郧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得众人对本部兵马都有着充足的信心,但一想到从此之后,所要对抗的对象是满洲大兵,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心下惴惴,不那么的有底气。
各种想法闪现的同时,众人全都看向了韩复。
韩复放下茶盏,抬眼看着刘苏,也是问道:“不知刘大人是愿做胡儿的那一个,还是不愿做胡儿的那一个?”
刘苏神情凝滞,垂下眼睑,低声说道:“下官身为南阳父母,纵有别样想法,若真是到了那一日,也无法以一己之念,违背众人之意。”
“不。”韩复摇了摇头,盯着刘苏的眼睛,再度问道:“本官不问别人,只问你刘大人。刘大人只须说自个愿是不愿即可。”
"。。。。。。"
刘苏埋低脑袋,死死盯着茶桌上纵横曲折的纹路,眸光不住变化,过了良久,才咬牙说道:“将军明鉴,下官虽是变节之人,但亦是读过圣贤书的。将军所办的那《襄樊抄报》,刊印有鞑子画像,下官观之,只觉如此形象,
虽为人,实与禽兽等同。若有的选,谁又愿做那弃祖宗冠裳,毁身体发肤的胡儿?只是如今情势如此,自闻皇爷潼关之败后,不说别的,便是伏牛山上的群寇,也都蠢蠢欲动,兵马四出,劫掠乡野。牛将军领兵东奔西走,到处灭
火,是以不曾来此面见将军。鞑子未来之时,已经如此,等鞑子真要南来了,我南阳又如何抵挡?本官就是再不情愿,但到了那一日,又有何办法?”
该说不说,这位南阳府尹,也算是个实诚人了。
虽然话语中还有所保留,但基本上说的都是实话。
鞑子大兵现在就在北面休整,但长则半年,短则一两个月,可能就要南下,到时候怎么办?
南阳这里只有牛万才一千多的兵马,算上最近几个月收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牌军,也不过两千之数。
这点家底,在几十万的满洲大兵面前,根本不够看的。
虽然大顺主力陆续从商洛山中撤出,但大顺在主力齐整之时,依托潼关都打不过鞑子,如今这点残兵败将,来到旷野之上,又怎么挡住鞑子的冲击?
况且,刘苏等人现在连李自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很难对他们抱有信心。
唯一能够依仗的上的,也只有南面的这个襄樊营。
他们刚才见过了,战力怎么样先不说,但襄樊营士卒所表现出来的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绝对是他们平生仅见。
刘苏咬着牙说完这番话以后,就怔怔地看着韩复,而韩复则用手指关节轻轻地叩着桌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偌大的茶楼内,一时没了言语,只有那“笃笃笃”的敲击之声,有节奏的响起,每一下仿佛都扣在众人的心头。
不知过了多久,那“笃笃笃”的声音停止,韩复端起茶盏,冲着刘苏和吴鄞等人举了举,笑道:“说好的是茶歇,怎地又谈起了这些俗务。来来来,喝茶,喝茶。
刘苏神色一黯,眸中光彩立时消失不见。
这次韩复到南阳来,共带了两支兵马保驾护航。
明面上的是以第四千总司为基础的,加强干总队。
而在暗处,则有魏大胡子的龙骑兵和赵栓率领的骑兵哨队一部,游弋在南阳附近,作为机动力量,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同时白河上,还有水营的船只往来巡逻,作为接应。
到了晚间,韩复依旧没有进城,而是驻在城外卧龙岗的军营当中。
这里据说是诸葛武侯在南阳躬耕读书的地方,韩复无从考证真假,但还是带着张全忠等人,恭恭敬敬参谒了武侯祠,给这位千古第一相敬了香。
而后就在武侯祠内,召开了前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