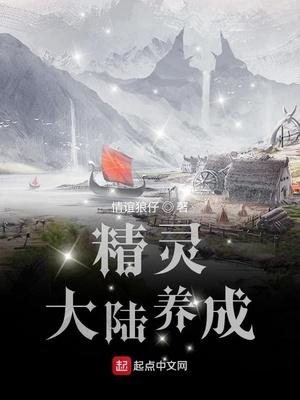笔趣阁>葬明1644 > 第214章 大厦将倾(第1页)
第214章 大厦将倾(第1页)
二月底,开足马力的阿济格大军,终于钻出了商洛山,破西峡口进入河南境内。
随即与聚集在河南的顺军兵马展开了激战。
李自成虽然自山海关开始,就一路失败,但不论是在山海关、山西、怀庆还是在潼关,李部都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主动撤出的。
大顺军的老营,始终没有受到重大创伤。
到这个时候,大顺各营的主力仍在,人数多达十万,是要高过阿济格、吴三桂和尚可喜这支西路军的。
只是由于一直以来的失败,使得顺军士气萎靡,况且这一次,大顺朝廷把根本之地的陕西也给丢了,他们是带着家眷跑路的。
于是,一旦战事陷入不利,甚至只是处于僵持阶段,大顺军不耐久战,军无固志的老毛病又犯了。
只要不能短期内取得胜利,他们下意识的就会选择逃跑。
不会死战到底,只想着避其锋芒。
既不是存人失地,也不是存地失人,而往往是又失地又失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撤退当中,庞大的集团逐渐走向了瓦解的命运。
清军的到来,引起了豫西一带士民官绅的极端恐惧,甚至伏牛山、秦岭上的土匪们也吓得抱头鼠窜。
清军要征发民夫,顺军要征发民夫,土匪转移之时,自然也会顺手劫掠一番。
豫西南大地上的劳苦大众们,又陷入到了极端的水深火热之中。
初战失利,使得在内乡等处停留了一个多月的大顺朝廷,终于开始慢慢腾腾的动作起来,准备继续向湖广转战。
离开之前,李自成下令屠城,史载“自成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人烟”。
这片仿佛被诅咒了的土地,又一次陷入到了真正的地狱之中。
当然,清军同样也不是善男信女,可很奇怪的是,顺军一直以来都处在清、明、顺这三方鄙视链的最底层。
清军自山西绕了一个大圈子一路追到江西,所到之处老百姓和官绅,大多都视清军为王师,而视李自成为流贼。
其实原因既无关阶级矛盾,也和民族大义没有关系,主要还在于清廷是统治者,是维护秩序的一方,而李自成是流寇,是破坏秩序,破坏生产的那一方。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坏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他们只想要安稳的过日子,谁当皇帝,他们都是一样的要交皇粮,没有区别。
这其实也是后来南明那些反抗清廷压迫的义士们,普遍面临的尴尬问题,就是老百姓拿他们当贼,把他们的反抗行为,当做是破坏秩序,破坏大家安稳过日子的野蛮行径。
会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消停点呢?
正是因为清楚的知道一旦清廷占据了统治者、秩序维护者这个生态位以后,局势将会对他们这些反抗者极为不利,所以韩复才很早的时候就开办报纸,做宣传,希望能够培育起民族意识,激发出民族主义这个大杀器。
不过,对于现在的李自成来说,他最先要考虑的,还是生存问题。
直驱南京的决议被顾君恩否决之后,李自成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曾经据有大半个中国的大顺朝廷,如今只剩下襄阳、德安这一小块根据地了。
除了到这里之外,没别的地方可去。
历史上,白旺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李自成大军到德安的时候,他凑吧凑吧,弄出了近七万人的兵马,随从李自成东去。
但本位面,由于出现了韩复这匹黑马,白旺原本的势力范围,被襄樊营划走了一大半,实力有所减弱,但也还有个三四万可战之兵。
这是李自成无论如何都要带走的。
时间进入三月,顺军这一次所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较之以往稍微顽强了一些。
加之山口地形比较狭窄,清军不便展开,双方还在密集的交锋当中。
大顺朝廷尚且还驻跸在内乡至邓州一带,还没有完全的撤离,韩复知道,要到三月中下旬,邓州之战彻底失败,李自成才会拔营而去。
不过对于韩复来说,此事已经不是他能够控制和更改的了。
韩复自从到南阳开始,几乎每日一封的给大顺朝廷,给永昌皇爷上书,分说天下大势,劝李自成早做预备,并且在每一封信的末尾,韩复都照例强调一下,请皇爷保重龙体,千万不要轻涉险地。
只是奏本呈上去以后,不知道是大顺朝廷已经陷入了瘫痪,还是他韩再兴人微言轻,总之是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半点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