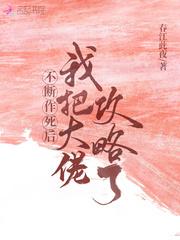笔趣阁>我要当大官 > 第二百二十五章 大清(第1页)
第二百二十五章 大清(第1页)
“燕赵二省,越发混乱,河南蔡恒龙屡次被官军镇压,但像是烧不死的野草一样,风一吹就又抖擞起来了。”
靠山堂,张良站在安昕桌案对面说道。
从燕赵、河南传回来的电报,加上对从河南、燕赵等地逃难到。。。
车子驶出塔什布拉克村三十余里,天色渐暗,沙丘的轮廓在暮色中如沉睡的巨兽般起伏。李燕靠在车窗边,耳机里循环播放着《最后一句》。那声轻笑像一根细线,缠绕在他心口,越收越紧。他忽然想起买买提老人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我唱完了,轮到你们说了。”那时病房里只有风穿过窗缝的呜咽,而此刻,车载音响将那句话反复重播,仿佛老人仍在耳畔低语。
手机震动起来,是苏婉发来的消息:“数据库今日完成第十二次情感拓扑建模升级。系统已能从残音中提取‘沉默的情感’??比如一声叹息前的停顿、哽咽时的呼吸频率变化。我们管它叫‘未言之言’。”
李燕盯着屏幕良久,指尖悬在键盘上,迟迟未回。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压在心底的悔、藏在眼神里的痛,终于也能被听见了。可他也清楚,技术越是逼近人心深处,就越容易触碰到禁忌的边界。他曾亲眼见过一位老妇人在听完丈夫五十年前一段录音后崩溃大哭??那是一封没寄出的情书,录于他们婚前夜,字字炽热,而她直到七十岁才知他曾如此深爱过自己。“早知道就好了……”她喃喃道,“哪怕只多一天也好。”
可“早知道”从来不是恩赐,有时反而是刀。
他摘下耳机,望向窗外。月光洒在戈壁滩上,银白一片,像是大地披上了旧时光的薄纱。远处,一辆卡车缓缓驶过,车灯划破寂静,又迅速被黑暗吞没。这让他想起邓伦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做的不是保存记忆,是在给时间打补丁??一块一块,试图缝合断裂的世代。”
回到省城已是凌晨。项目总部大楼依旧灯火通明。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几位研究员正围坐在全息投影前,调试一段来自云南怒江傈僳族村落的录音。画面中,一位百岁老人用颤抖的手指敲击铜铃,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古歌。AI分析显示,这段音频的情绪波动曲线呈现出罕见的“双峰共振”现象??即悲伤与喜悦同时达到峰值。
“她在唱送别,也是在迎新。”苏婉站在投影旁解释,“歌词大意是:‘我的眼睛看不见明天,但我的声音会替我看。’”
李燕默默听着,忽然问道:“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改变某些东西?不只是记录,而是……干预?”
苏婉转过头看他:“你是说,这些被倾听的人,开始活得不一样了?”
“不止是活法。”他低声说,“是自我认知。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故事值得被存档、被传播、甚至被孩子写进作文里,他会重新审视自己这一生。就像吐尔逊娜依医生说的??‘原来我的声音这么轻,可做的事一点都不轻。’这不是技术反馈,是尊严重建。”
苏婉沉默片刻,打开终端调出一组数据:“过去半年,参与‘家音课’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平均下降37%;农村地区青少年对祖辈的理解度提升52%;更有意思的是,有14个村庄出现了‘反向传承’现象??年轻人主动向老人学习民谣、方言和手工艺,并录制上传至平台。”
她顿了顿,嘴角微扬:“最离谱的是贵州雷山一个苗寨,去年还因为年轻人外流差点变成‘空心村’,现在反倒成了‘声音旅游示范点’。城里人专程跑去听老人唱歌,住吊脚楼,吃酸汤鱼,临走还要买一张刻录了家族口述史的U盘当纪念品。”
李燕忍不住笑了:“所以我们的文化抢救工程,最后变成了乡村振兴项目?”
“不。”苏婉摇头,“是我们忘了,真正的振兴,从来不是修几条路、盖几栋房就能实现的。人心要是断了根,房子再新也是废墟。而现在,有人开始愿意回家了??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那一段等他来听的声音。”
两人并肩站在窗前,望着城市灯火如星河倾泻。李燕忽然问:“你说,如果有一天,整个国家的记忆都被数字化了,会发生什么?”
“你会害怕吗?”苏婉反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北京论坛上的小女孩,她说“他也暖”的样子,像一束光照进他心里最幽暗的角落。他又想起盲妇的话:“我现在不怕死了。”还有小男孩写的歌词:“我把阿娜尔汗的故事唱给全世界听。”
良久,他说:“我不怕遗忘,我怕的是……当我们拥有了记住一切的能力,反而失去了选择的意义。谁该被记住?什么才算重要?如果我们把每个喷嚏、每句牢骚都录下来,那真正的声音会不会被淹没?”
苏婉轻轻点头:“所以我们加了‘情感权重算法’。不是所有声音都能进入核心库。系统会根据共鸣强度、代际传递潜力、社会价值维度进行筛选。就像河流过滤泥沙,留下清流。”
“可谁来决定权重?”李燕盯着她的眼睛,“是你?是我?还是某个躲在后台的审查员?”
空气骤然凝固。
苏婉避开视线,声音低了几分:“上级部门确实在讨论建立‘记忆伦理委员会’。初步设想是由学者、民众代表和技术专家共同组成,负责制定收录标准和使用规范。”
“听起来很民主。”李燕冷笑,“可一旦涉及权力,民主往往只是装饰。还记得三年前那个维吾尔族老铁匠吗?他录了一段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饥荒的回忆,刚上传就被自动屏蔽,理由是‘内容敏感’。我们争了整整两个月,最后删掉两句话才放行。可你知道吗?那两句话是他最想留下的??他说他爹抱着饿死的妹妹哭了三天,却不敢埋,怕被人发现家里断粮会被批斗。”
“那是特殊情况。”苏婉辩解,“平台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法律可以修改,人心不能打折。”李燕语气陡然严厉,“如果我们连痛苦都要剪辑,那还有什么真实可言?‘忆’项目的初心是什么?不是粉饰太平,是让每一个普通人敢于说出‘我存在过’!可现在呢?我们一边建声音小屋,一边设防火墙;一边鼓励老人开口,一边悄悄删他们的真话!”
会议室陷入长久的沉默。
窗外,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紧接着雷声滚滚而来。暴雨毫无预兆地砸落,敲打着玻璃幕墙,如同万千手指急切叩门。
苏婉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掩盖:“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我更怕另一种结局??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妥协,项目根本活不到今天。你想想,是谁批的资金?是谁给的政策支持?没有体制的庇护,我们连一台服务器都架不起来。”
李燕闭上眼,深吸一口气。他知道她说的是事实。这个项目从诞生之初就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像一根绷紧的弦,稍有不慎便会断裂。他曾因坚持收录一段藏区牧民讲述文革遭遇的录音,险些被撤换负责人;也曾为了保住西北某村集体传唱的抗税民谣,不得不答应为地方政府制作一部“正能量乡土宣传片”作为交换。
理想主义者要学会弯腰,否则连站直的机会都没有。
“我不是要推翻规则。”他睁开眼,语气缓了下来,“我只是希望,底线别丢。我们可以删减,但不能篡改;可以延迟发布,但不能永久封存。至少……给他们一个‘暂存密室’,让未来的人有机会看到原本的样子。”
苏婉看着他,许久,轻轻点头:“我已经在系统底层设置了‘灰域档案’。所有被拦截的内容都会加密存储,设定七十年后自动解密。钥匙由三人分别保管??你、我和邓伦。除非三人一致同意,否则无法提前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