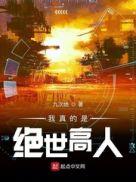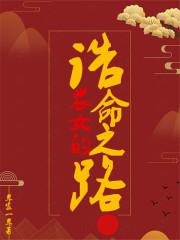笔趣阁>我要当大官 > 第二百二十六章 子弹日产量(第3页)
第二百二十六章 子弹日产量(第3页)
两人愣住。
“什么意思?”
“把关键录音转译成口传文本。”李燕眼神坚定,“找一批可信的讲述者,让他们背下来,一代代传下去。就像古代的史诗吟游诗人。只要还有人在说,声音就不会灭。”
邓伦缓缓睁大眼睛:“你是说……重建oraltradition(口头传统)?”
“对。”李燕点头,“文字会被焚,磁盘会被毁,但人心记下的东西,最难抹去。我们可以挑选各地志愿者,每人负责一段,定期轮换内容,形成网络。哪怕未来全面清查,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起来。”
苏婉喃喃道:“这简直像是回到了青铜时代……可也许,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一个月后,“声音种子计划”悄然启动。首批五十名讲述者分布在新疆、西藏、内蒙古、贵州、黑龙江等地,身份各异:乡村教师、寺庙喇嘛、边境护林员、非遗传承人、甚至一名在押服刑人员??他曾是1980年代某高校学生运动亲历者,狱中自学心理学,现为监区心理辅导员。
每段录音被拆解为三百字以内的精简版本,配以特定记忆符号和韵律节奏,便于长期记忆。例如,伊宁教师请愿事件被浓缩为一首十二行诗:
>“春寒料峭雪满城,
>三十先生叩府门。
>字字血泪求书声,
>一纸批文断前程。
>枯井无言埋忠骨,
>黑榜除名讳姓名。
>至今校园风起处,
>犹闻朗朗读书声。”
讲述者需每月通过暗语通话确认存活状态,若有失联,则自动触发内容转移机制。
与此同时,公众对“忆”项目的热情持续高涨。六一儿童节,全国中小学生同唱一首新创歌曲《听爷爷说话》,歌词源自平台精选的百条祖辈语音片段。央视播出特别节目,镜头扫过一个个家庭围坐聆听老录音的场景,millionsviewerstears。
然而,在这温情背后,暗流汹涌。
六月中旬,邓伦在赴青海调研途中遭遇车祸,所幸仅受轻伤。但事后调查发现,刹车系统被人动过手脚。同一周,苏婉家中电脑遭黑客入侵,部分非核心数据库被窃取并恶意公开,其中包括几位老兵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导致他们接连收到恐吓电话。
李燕明白,敌人已经开始反击。
七月流火,他在甘肃敦煌主持一场“丝绸之路声音遗产论坛”。闭幕式上,他站在月牙泉畔的露天舞台上,面对数百名学者、艺术家与普通民众,第一次公开谈及“记忆的政治”。
“我们常以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说,“但我想告诉你们,真正决定历史能否留存的,往往是那些默默按下录音键的人。不是帝王将相,不是史官御笔,而是某个深夜守在病床前的女儿,是某个蹲在田埂上录爷爷讲故事的少年。他们才是文明的守夜人。”
台下掌声雷动。
就在此时,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加密消息,来自贵州那位苗寨祭司的孙子:
>“阿公昨夜去世。临终前让我告诉你:‘树倒了,根还在。风带不走种子,因为它藏在鸟的喉咙里。’”
李燕仰头望向星空,沙漠的夜空清澈如洗,银河横贯天际,宛如一条流淌着亿万声音的河流。
他知道,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但他也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听,就永远有人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