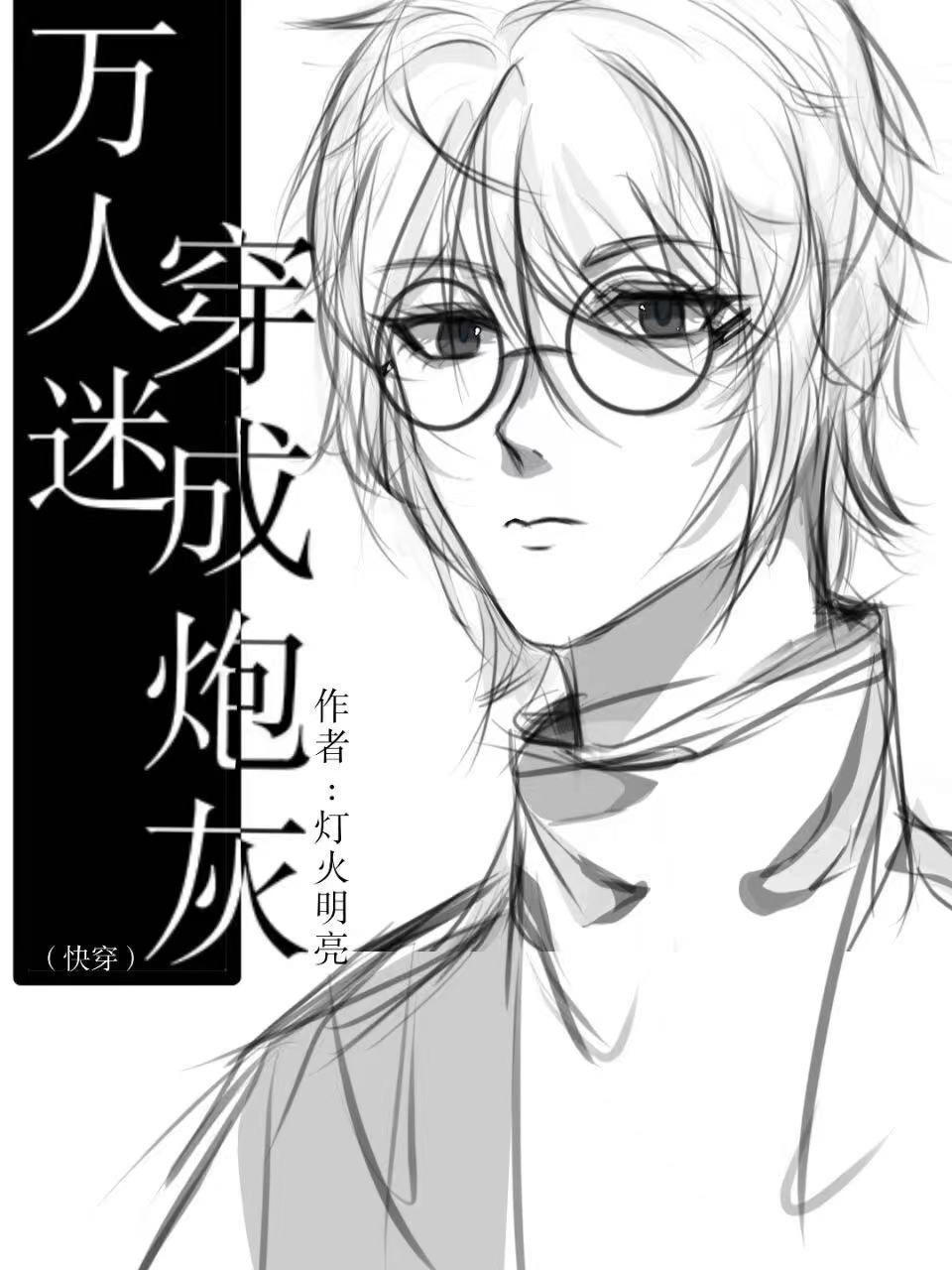笔趣阁>与君同岸 > 归来(第1页)
归来(第1页)
不知过了多久,陆子白早已忘记了那个名字。
一个特别的名字,一个曾经响彻天下的名字。
那人仿佛早就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也从这人世间悄然隐去。
六月三十的夜晚,陆子白照常躺在床上,闭眼入眠。
梦中,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句话。
“再见。”
那人轻声说,语气温柔极了。
次日清晨,陆子白睁开眼。
眼前模糊一片。
“滕九皋死了。”
?
“小公子,这话可不能乱讲……胡说八道是要折寿的!”小远慌张地劝着。
可陆子白却笑了。
他像是被某个笑话逗乐了似的。他甚至想高兴地坐起,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边嘴角一动不动。仿佛被什么钉在原地。
他伸手去摸,右脸毫无反应。
只有左边脸颊,不合时宜地牵扯出一个僵硬,扭曲,像哭像笑的弧度。
“……我右脸,动不了了。”
医师来了。
他替陆子白把了脉,又点了几处穴道。
不一会,陆子白的右脸终于缓缓动了动。
“……小公子肝气郁结。昨夜哭得太久,情绪滞留,邪气乘虚而入,才导致一时面部僵硬。”医师拱手退下。
室内重新归于沉寂。
不久,米莲华拎着药罐走进来。她在陆子白床边坐下,轻轻为他理了理垂落的发丝。
“遐哥儿,娘知道,你担心朋友的安危。”
“他死了。他不是我朋友了。”
米莲华手一顿,轻轻顺了顺他后背。
“你给他写封信,好不好?娘帮你送。”
“他收不下了。他已经死了。”
“遐哥儿,休要胡言。”
可陆子白却猛地抬头,那双眼睛又红又干,像是哭到再无眼泪:“我看见他了。他说,再见。他就是死了,死人才会托梦。”
“遐哥儿,你先写信,回来娘帮你送。”
下午,陆子白趁着无人使唤,便下床,提笔,写了整整五页歪歪扭扭的信。
信上写了他与滕九皋的相认,相识,相知。里面也有他对滕九皋的猜忌,与质问。
「你为何帮我追查卢武倾?天底下哪会有人如此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