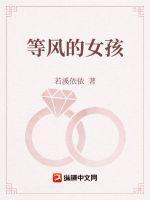笔趣阁>暮光之找到我 > C 都给我滚(第2页)
C 都给我滚(第2页)
“进来。”我说。
门开了,他的眼睛低垂着,不敢看我。
我把火柴盒扔过去,“点起来。”
“阿罗大人说——”
“shh。”
他闭上嘴,听从指令擦燃火柴,火焰在木条的末端跳动。我盯着那根东西看了两秒钟,然后让卫士将它弹进了壁炉。
干柴劈啪响了几声,壁炉起了火光。卫士后退了几步。
“退下。”我没看他,“告诉阿罗,由他怎么审,只要别来敲我的门。也别再派任何人来打扰我。”
门重新关上,房间里只剩下我和火焰。
矿物颜料味,茶块,松脂——壁炉的暖气将气味烘托上来,这里的空气浑浊不堪。
她说的那幅画还立在画架上,就在靠窗的位置。她一坐在那儿就不会移动。时不时发发善心走过来,拧着眉头瞥了眼我手中的希腊文便摇头走开。我好心地教她发音,她抬手就捂起耳朵。
那是一幅海景,蓝色的海,她在我离开的那几天画的,上面没有我。
我走到画前,油画已经干透,但是她没来得及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上光油。油画的保护层,让颜色持久的东西。
“我亲爱的弟弟。”阿罗出现在门口,“你从来没缺席过审判。”
我转身,他穿着黑色的令人厌烦的西服,脸上是陈旧的微笑。我从没像今天这样厌倦他那优雅陈腐的作风。
阿罗走近了,眯着眼睛仔细端详她的画,头微微偏向一侧,嘴中念念有词:“那个倔强的年轻人确实有才华。伦勃朗和透纳的信徒……”他伸出手,似乎想触碰,我冷眼把画抽走。
阿罗笑道:“我们的收藏室里有上好的达玛树脂。比松香更稳定、柔韧,不易变黄,我可以派人送来。”
“不过,或许我们可以之后再做这件事,我相信你会对这起案子感兴趣,一个吸血鬼小说家,他在文中透露了我们这个血族世界的细节。哦,但是,但是,相信我,他的文字是优美的,这个新型罪犯才华横溢,我们可以为他换种惩戒方式你说对吗?”阿罗微笑,他看起来跃跃欲试,是的,他又找到了乐子。
厌腻的笑容。
我烦透了。走回壁炉前,我咧嘴向他笑,露出尖牙:“那就让他去死。”
“弟弟。”阿罗轻描淡写,“不过是个不安分的年轻吸血鬼,在佛罗伦萨引起了不必要的注意,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伤害,小事而已,我们应该对年轻艺术家多些宽容。但我们的律法,既定的审判需要三位长老同时在场,这是规矩。”
“你在为他开脱吗?”我冷嘲。
“哦,不。我承认我对艺术的喜爱与痴迷,毕竟这位年轻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应该将他纳入沃尔图里,让他整理文献室里的东西。要知道那些手稿已经尘封了几个世纪,我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人类过于麻烦,很少有吸血鬼如此热爱文学和历史——”
“我不在乎那个蠢货会写什么,让他滚。”
“审判厅从来没有空椅。”阿罗笑容依旧,“这不符合法律。”
“你和马库斯可以裁定。”
房间里静了一瞬。火焰在壁炉里静静涌动。
“凯厄斯,弟弟——”阿罗的声音沉下来,又要开始他那套长篇大论的劝说。每一次歼灭,斩草除根的建议都以这类可笑的仁慈被劝阻。现在好了,又多了几件蠢事耗费我的时间。
怒气升腾到眼底,我不耐烦地旋身,“阿罗——”该死的,我提声笑起来,獠牙森痒,手指不自觉地去寻找可以捏碎的东西,可是目光所及,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她带来的——除了阿罗那颗无所事事,玩物丧志、无可救药的头颅。
“哥哥,你快把我烦死了。”
阿罗一边说话,一边动作,布料相互接触发出恼人的刮擦,还有他的步伐,该死的慢动作,文艺复兴时期沉迷歌剧养出的坏毛病。
“你已经有段时间没去试炼场了。卫士们在议论。”他说。
“那就让他们滚。”
“你的存在至关重要,凯厄斯,只有你能让我们的卫士们信服,还有一周,或许我们不该让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分心,而且,还有一些新生儿要处理。”
“分心?”我的耐心已经见底,“阿罗,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才能试着克制你那些不务正业的心思,为什么——任何一件蠢事都要我亲力亲为!”
舌尖刮过尖牙,我咽下毒液,焰火让我的皮肤发烫,鼻尖又回味起她手上的硫磺味。
“宴会,交际,掌声,想想那些滑稽的事情,你沉溺于不知所谓的附和与虚伪的嘴脸,还有那些雕塑!藏画!告诉我,亲爱的哥哥,谈天论地除了能给你和那些空虚的朋友带来一些虚假的崇高还能带来什么?时代和主义的陈词滥调你还没听够吗,他们甚至都不真正了解和在乎从自己口中吐出的东西。”
我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你要是能从那些不切实际的艺术家信友里回过神来,我需要处理的烂摊子就不会这么多。”
“你这是在怪罪我吗,弟弟?”阿罗无辜地撇下眉轻声呢喃。
“怪罪?”我冷笑,“哦是的,哥哥,谁叫你一开始就粗心大意地把她给弄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