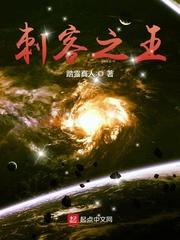笔趣阁>物色 > 第 525 章(第1页)
第 525 章(第1页)
时悲从中来,眼皮烫得能流出血水。
宋显义风光了大半辈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临了,竟然走得这么不体面,他生前最爱干净,从未邋遢过。
当时她在奥克兰坐牢,没能来得及送他最后一程,这一直是她莫大的遗憾,抚触宋显义的照片,她吸鼻子,默默落下泪。
江宴行单手搭她肩膀,见她冷淡避开,又取出块手帕巾强行塞她手里,“眼泪汪汪的,怎么看得清你爸?”
“这是最后一次带你来南山。”他的腔调意味深长。
宋栖棠深吸一口气,胡乱擦了擦眼睛,继续看宋显义被羁押的视频,短短三十秒,她看得非常认真,周而复始地循环。
江宴行盯着视频,忽而看向监狱长,“之前的监狱长呢?”
“您说任雄?得了肝癌,几年前就死了,年纪轻轻的,没想到得这么个病,家里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就是他,您看,光从外形判断,他真不像癌症病人,”监狱长指着视频中的男人,“那时噩耗传出来,我们都不信。”
江宴行不置可否,再次审视视频。
视频里,宋显义一样样卸下身上的手表、袖扣,身边站着孔武有力的任雄,他的目光偶尔掠过镜头,像锐利的鹰隼。
彼此隔着视频相接视线,江宴行脸色冷然,眯了眯眸子。
他俯身的时间太久,温热气息绵绵不断喷洒宋栖棠颈侧,撩起她耳边碎发,若有若无的痒意蔓延。
她疑惑侧眸,“怎么了?”
两个人靠得太近,嘴角险些碰上。
明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盘旋的尘埃轻盈沾到她额头,眼睛点漆一般黑,聚焦着璨璨的光圈。
他位于光圈正中央,眉梢眼角流动熠熠光辉。
色字头上一把刀,还是柄岁月静好的温柔刃。
在监狱这种阴暗冰冷的地方,居然还能想到岁月静好这个词,也是服了自己。
江宴行喉结滚了滚,把她黏耳侧的细发勾耳后,“没事。”
宋栖棠接着转头看视频。
看着宋显义孤零零坐在监狱角落,心酸无论如何都忍不住。
过了一会儿,她努力平复心绪,又听江宴行语气寻常问监狱长,“任雄现在的家庭情况如何?”
“不太好,老婆是血友病患者,生活全托社区照顾。”监狱长显然很同情任家,“我们单位也有相应津贴,可惜杯水车薪。”
宋栖棠隐隐觉得古怪。
江宴行貌似非常关注任雄。
可任雄好像没值得怀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