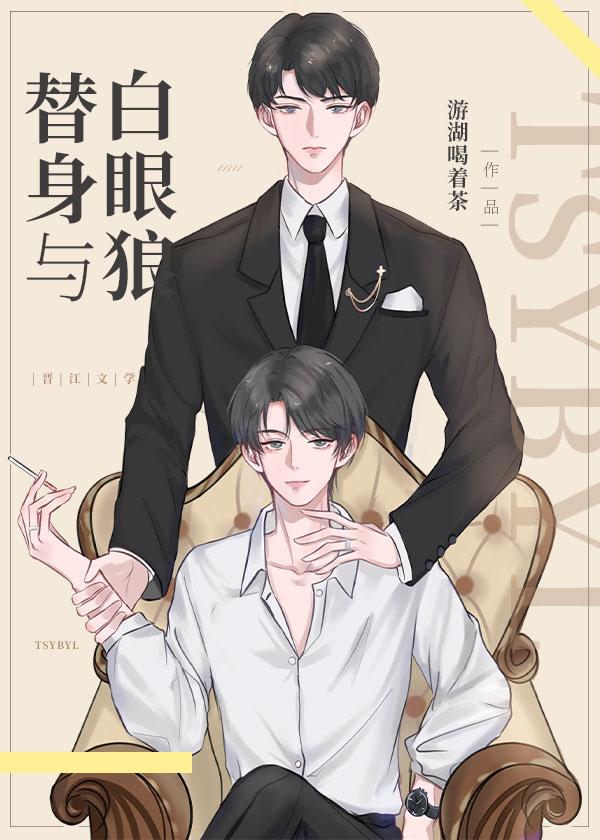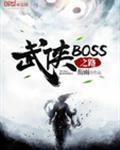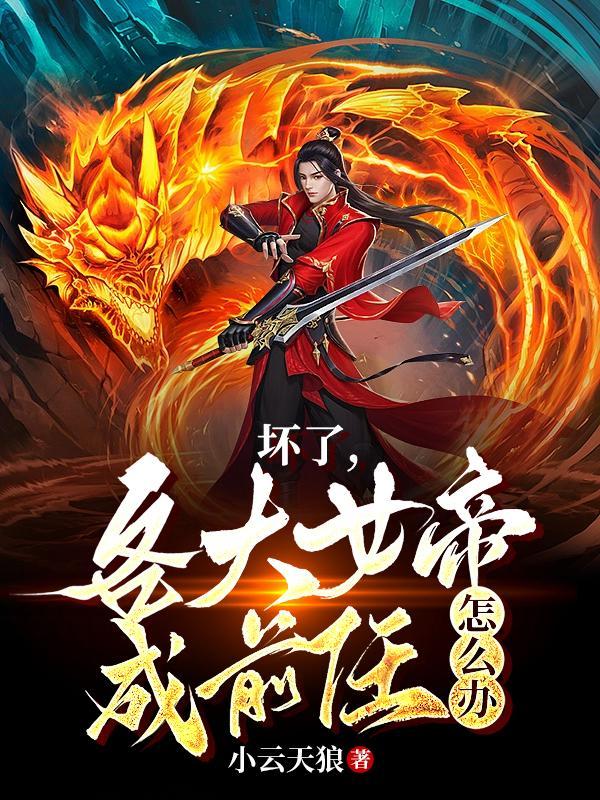笔趣阁>虎贲郎 > 第764章 墙倒人推(第2页)
第764章 墙倒人推(第2页)
>“吾儿近日常问:‘曹叔何时回宫吃饭?’我说,等稻子熟了。他便每日去御花园看那一小片试验田,说要替曹叔守着收成。”
曹霖读罢,久久无言。他想起十年前初入朝堂时,那位瘦弱的小皇帝拉着他的衣角,怯生生地问:“先生,我能吃饱饭吗?”如今孩子已长高许多,却仍记得那个承诺。
他提笔回信:
>“请转告陛下:待来年麦浪翻金,臣必携新粮归京,与万民共尝第一釜白米饭。”
信毕,命人将当年在展宏原烧毁的地契灰烬取来,装入锦囊,附于回使马侧。他知道,那团灰烬比任何玉玺都更沉重??它是无数人重生的见证。
春耕全面铺开之际,北方突传战讯。匈奴别部乌桓乘雪化河开,袭扰雁门关外屯田区,焚毁粮仓两座,劫走耕牛三百余头。边军出击受挫,主将重伤。消息传来,举国震动。
许多人以为曹霖会怒发兴兵,谁知他只是召集群臣议事,提出一项惊人计划:不派大军,改派一百名地工、五十位民医、三十位织匠,携种子、农具、药品北上,在边境设立“安边十屯”,实行军民共耕。
“敌人烧我们的粮,我们就种更多。”他说,“他们怕百姓有地,我们就让每一寸荒原都长出庄稼。用锄头筑防线,比用刀枪更久远。”
众人愕然。有将领质疑:“若敌再来劫掠,岂非资敌?”
曹霖反问:“若百姓无粮,谁愿为国戍边?今日我们护的不是几座仓,是人心。只要人心不溃,纵使一时失粮,终能复耕;若人心散了,纵有百万甲士,也不过空壳一座。”
最终方案获批。曹霖亲赴雁门,在长城脚下选址建屯。他与士兵一同搬石砌墙,手磨出血泡也不停歇。夜间宿营,他与老兵围炉夜话,听他们讲边塞苦寒、家人离散。一名老兵哭诉:“我家闺女去年饿死了……就因为县官把救济粮卖给了米商……”
曹霖默默记下姓名籍贯,次日即下令彻查该县官,查实后立即革职充军,并责令退还赃粮三倍。
十屯建成之日,正值清明。曹霖主持祭礼,不祭战魂,唯祭亡农。他命人列出历年因饥荒、苛政、战乱而死的农民名录,长达百卷,一一诵读。最后,他点燃火把,将名册投入青铜巨鼎。
火焰腾起时,他对万名军民说道:
“今天我们不拜鬼神,不颂帝王。我们只记住一件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粒米,都浸透过血与泪。谁若敢让它荒芜,就是与天下苍生为敌。”
话音落下,全场寂静。继而,万千锄头同时敲击地面,声震山谷,如同大地的心跳。
与此同时,泰山归心碑前再起异象。那九朵青莲竟结出果实,形如谷穗,散发淡淡金光。果实落地即化为九块玉牌,每块刻一字,合为一句:
>**“耕者有其田,乃天下太平之基。”**
此语传开,民间争相誊抄,甚至有工匠将其铸于铁犁之上,称为“犁铭”。
夏末,南方传来喜讯:岑娘子主持的岭南药园成功移植槟榔、肉桂、丁香三种热带作物,并研制出新型防疫药丸,可预防夏日瘟疫。首批十万粒分发荆楚地区,疫情骤减七成。百姓感念,尊称其为“南药圣姑”。
而在西北,阿咄率领匈奴各部迁徙至河西走廊,依曹霖所授农法开垦绿洲。昔日游牧之地,如今阡陌纵横,稻麦飘香。匈奴孩童入学堂,学汉字、算术、农政律令。阿咄致信曹霖:“吾族百年逐水草而居,今始知定居之乐。愿子孙永为农人,不复为寇。”
秋收再度大丰。全国十八州粮产突破三亿石,义廪之外,另设“活命仓”“备荒窖”“种子库”三级储粮体系,确保三年内即便大灾亦不断炊。米价稳定在每石三十钱上下,百姓安居乐业。
这一年除夕,曹霖未归展宏原,而是巡行至最偏远的武陵山区。此处山高路险,历来贫瘠。他带人凿岩开道,引溪灌田,建成梯田三百亩。除夕夜,全村聚于祠堂,以粗米饭、野菜汤设宴,请曹霖上座。
一位盲眼老妪摸索着端来一碗饭,双手颤抖:“这是我孙儿第一次吃饱的年夜饭……请您尝一口,替我们谢天谢地。”
曹霖接过碗,低头吃下一口。饭糙且冷,却觉从未如此甘甜。
当夜,他在村塾墙壁题诗一首:
>“莫道深山无日月,
>一灯照处即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