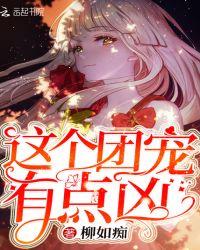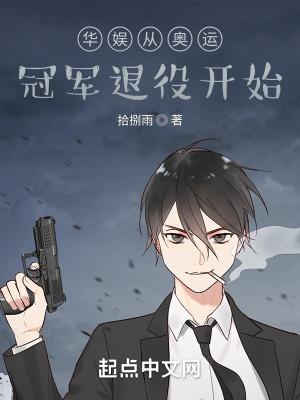笔趣阁>柯南:我真觉得米花町是天堂 > 第424章(第2页)
第424章(第2页)
>“你觉得幸福吗?”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什么都不想。”
>“你不难过?”
>“难过是什么?”
>“你会想念亲人吗?”
>“没必要。他们也很平静。”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打断:
>“这是我丈夫!他一个月前失踪了!他说要去参加一个‘心灵净化营’,回来就这样了!医生说他生理指标完全正常,可他已经不认识我和孩子了!”
音频结束。
纪一呼吸沉重。这不是情绪抑制,这是人格抹除。
>“他们不再阻止你发声,”千穗说,“他们让你说话,但说的是他们写好的台词。你笑,是因为程序告诉你该笑;你流泪,是因为系统触发了悲伤模拟模块。真正的你,已经被替换了。”
纪一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米花町的灯火依旧温暖,孩子们的噪音节还没结束,远处还能听见鼓掌声和笑声。可此刻,这些声音在他耳中变得陌生起来??它们是否也正被悄然渗透?那些看似自发的情感流露,会不会早已被预设了节奏与强度?
他打开电脑,接入“声音档案馆”的深层数据库,启动一项从未公开的功能:“共鸣溯源”。
原理很简单:每个人的声音都有独特的生物特征,就像指纹。当一个人长期收听特定音频,其发声模式会发生微妙趋同??语速变缓、音域收窄、情感起伏减弱。通过比对数百万条公开录音,他可以绘制出“声音同化地图”。
结果令人心悸。
东京、大阪、福冈、札幌……主要城市的核心区域,呈现出大片粉红色斑块,代表“高程度语音趋同”。而在郊区或偏远村落,颜色逐渐转为绿色??健康差异性。
最恐怖的是,这些粉红区域的扩散轨迹,与“森之息”产品配送路线完全重合。
“他们用商品铺路。”纪一喃喃道,“茶、香薰、枕头内置扬声器、儿童睡前故事机……全都是载体。”
他立即拨通灰原哀的号码。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黑进全国三大物流公司的冷链追踪系统,查所有标有‘易碎品?恒温保存’的包裹,目的地为学校、养老院、心理咨询中心的优先排查。”
>“你要找什么?”她问。
>“活体音频植入装置。可能是胶囊,也可能是贴片,能通过消化道或皮肤吸收,直接作用于听觉皮层。一旦激活,使用者就会无条件信任所听到的‘温柔声音’。”
挂断电话后,他翻开母亲留下的笔记本残页。其中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群年轻人站在实验室门口,笑容灿烂。母亲站在中间,手里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而在她身旁,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正是年轻时的林田由纪。
背面有一行小字:
>“1995年夏,‘自由声波计划’成立日。我们相信,每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哪怕它颤抖、破碎、令人不适。因为正是这些声音,构成了人类的尊严。”
纪一闭上眼。
他曾以为这场战争是技术对抗,是数据攻防,是服务器之间的明争暗斗。但现在他明白了,真正的战场,从来都在人的耳朵里,在每一次选择倾听谁、拒绝谁的瞬间。
第二天清晨,一封匿名邮件抵达日本各大主流媒体邮箱。
附件是一段九分钟的音频,标题仅两个字:《醒来》。
内容没有任何旁白,只有纯粹的声音拼贴:
-产房里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
-战地记者临死前按住录音键说出的最后几个词;
-一位抑郁症患者在跳楼前二十分钟给热线打去的电话,全程沉默,只有呼吸;
-还有纪一母亲的最后一段日记结尾,那句“哪怕只剩下一口气,我也要吵下去”,被放慢十倍,变成一种近乎祷告的低语。
整段音频经过特殊处理,含有隐秘的脑波共振频率,能短暂打破“情感稳态”状态下的神经屏蔽效应。
播出后不到六小时,全国共有三百二十一人拨打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创下历史峰值。更有数十名曾参与“心灵净化营”的志愿者主动自首,称自己“感觉像睡了三年,刚被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