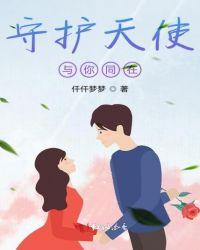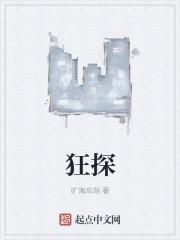笔趣阁>出宫前夜,疯批帝王后悔了 > 第487章 她的眼里只有他(第2页)
第487章 她的眼里只有他(第2页)
三日后,长安城西门。
街头巷尾张贴着新颁布的《清明言会条例》,百姓围聚议论,神情复杂。有人欢喜,有人恐惧,更有几位白发老臣站在太庙碑林前久久不语,手指颤抖地抚过那些刚刚刻上的名字。
晚芜没有走正街,而是由一条隐秘小径进入皇城废墟。紫宸殿早已焚毁,只剩残垣断壁,野草丛生。唯有那根象征皇权的蟠龙柱尚立着,柱身焦黑,裂缝中竟开出几朵白色小花。
赵德全住在偏殿角落的一间陋室里,瘦骨嶙峋,气息微弱。见到晚芜那一刻,他浑浊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清明,挣扎着要起身叩拜。
“不必。”晚芜扶住他,“我不是皇后,也不是公主,只是一个想听真话的人。”
老人喘息片刻,终于开口:“那夜……雷霆交加,皇后难产。接生嬷嬷发现胎发乌黑浓密,初以为得男,欢呼声刚起,裴世衡便带着太医冲进来,说脉象显示胎儿先天不足,需立即移出调养。我们不敢违抗,只能眼睁睁看着襁褓被抱走……可后来我才知,那孩子根本没病,她是被人调换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真正的皇子,脐带上缠着一道红绳??那是祖制,以防妖祟夺魂。而那个被宣称夭折的‘皇子’,身上没有红绳。反倒是后来宫中悄悄接入的‘太子’,脚踝内侧有颗朱砂痣,与皇后族谱记载完全不符。”
晚芜静静听着,心口如压巨石。
“皇后临死前,咬破手指,在衣襟写下‘吾女尚存,勿忘归期’八字,交给我藏好。可第二天,裴允衡便派人搜查所有近侍居所。我怕连累家人,只好烧了血书,只将内容默记于心……这些年,我日日诵念,生怕忘了。”
他枯槁的手抓住晚芜的袖角:“姑娘,你……你是不是就是她?是不是那个被送出宫的孩子?”
晚芜没有回答,只是从怀中取出一枚玉佩??那是她在南诏地宫深处找到的,背面刻着“晚芜”二字,材质与皇后凤冠上的碎玉一致。
赵德全盯着玉佩,老泪纵横,猛地伏地叩首:“臣……终于等到您回来了!”
她扶起老人,轻声道:“我不是回来争位的。我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历史不该由胜利者书写,而应由幸存者铭记。”
当晚,她留在陋室中,彻夜整理赵德全口述的内容,并命人誊抄九份,分别送往各地学府、史馆、民间书院。她在文末亲笔添上一句:
>“我不是为了证明我是谁而活着,而是为了让千万个无法发声的人,重新拥有说话的权利。”
归途之中,天降大雨。
马车行至半山腰,忽闻前方传来喧哗声。数十名百姓拦路跪拜,为首者是一位中年妇人,怀抱一只褪色襁褓,泣不成声。
“昭明夫人!”她磕头至额角渗血,“我夫君是边关校尉,三年前因上书揭露军饷贪腐被捕,从此杳无音讯。昨夜我梦见他胸口挂着铜铃,不断震动,似有话说……求您让我听听他的声音!哪怕只一句也好!”
晚芜下车,搀起妇人,带回铃屋。她点燃魂灯,将忆鉴镜对准那枚从梦中“取回”的无形铃铛,割指滴血于阵心,低声吟唱南诏古调。
良久,铃声微颤。
一道沙哑而熟悉的男声缓缓响起:
>“阿芸,对不起……我没守住诺言。但他们逼我认罪时,我没签字。最后一刻,我想的是你们母女吃上了新米没有……孩子要是问我爹去哪儿了,就说……就说我在守边疆。”
妇人瘫坐于地,嚎啕大哭。片刻后,她擦干泪水,从怀中掏出一支炭笔,在墙上用力写下三个字:**“不说谎”。**
此后数月,类似之事屡见不鲜。有人听到了战死亲人的遗言,有人确认了家族蒙冤的真相,更有甚者,通过铜铃接收到了来自未来的警示??一位老道士声称,他在镜中看到了五十年后的长安,满城皆立“沉默碑”,人人低头疾行,无人敢言往事。他惊醒后立刻前来求教破解之法。
晚芜沉思良久,召集南诏长老与民间智者,共议设立“传音塔”计划:在全国七十二州各建一座高塔,内置忆鉴镜与共鸣铃,由专人值守,定期举行“回声祭”,确保亡魂之声得以流转不息。
与此同时,关于她的传说也在悄然演变。有人说她是重生的皇后,有人说她是天地派来的言灵使者,甚至有孩童编出童谣:
>“铃儿响,夜不长,晚芜姐姐照四方。
>谁若欺心藏假话,铜镜照出黑肚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