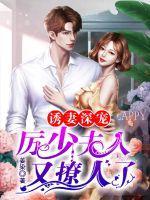笔趣阁>被朝臣听到心声后 > 3040(第9页)
3040(第9页)
等到谢兰藻离去后,一道手诏送去御史台,此后御史可不经御史大夫,独自弹劾奏事。
本朝旧制,但凡纠弹百官事,御史得先言于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兼任京兆尹,又带知政事的相衔,是政事堂宰相之一。此制一改,御史台官员便不经宰臣,能直达天听。
第35章
太庙壁中天书给朝臣带来的压迫极大,一门心思地想要探听宫里头的情况。只不过在工部尚书和将作大匠出来后,知道是要制造什么东西,除了户部尚书拉长了脸外,其余人立马就没兴趣了。
跟国子监改制无关,不用管。
看一次“天书”,就想回家撸起袖子打孩子。如果不是他们闹腾,如果不是他们恰好斗到陛下跟前,会惹出这么一档子事吗?甚至连诸帝之灵都惊动了啊!
陛下是真龙之体,当真如神明降世,可真要那么改——置往日“体统”于何地呢?事情牵扯的东西太多,群臣不敢大声议论,就连刚直的御史和谏官都呈现出了一副缩着脖子的柔服之态。千言万语不得说,过去靠着“祖宗之法”四个字压别人,现在倒是自己被掐住了喉咙。
可真要他们闭嘴又是彻底不可能的,待到翌日上朝的时候,朝臣们将苦涩藏在心里,面上仍旧一副端肃刚正的凛然之态,禀告道:“国子监法度缺失,理应改制。只是诸帝高居玉台天阙,与人间事久违。改制之事,得应时而变。”
说话的人恭恭敬敬的,可赵嘉陵听着眉头微蹙。
明君系统贴心翻译:【这位大臣的意思是,死干净点,别管人间事。】
那保守派臣子心脏一抽,吓得面无人色。膝盖一软,险些跪倒在地。
他哪有这个意思?神明在上,怎么可以栽赃陷害啊!
诸帝的体面其实赵嘉陵是不在意的,但她毕竟是皇帝,诸帝等同于她的颜面。她望向了保守派臣子,轻飘飘道:“看来卿久在人间,知众生疾苦。国子监如此风气的,想来也在卿眼中了?怎么先前不将此事上禀?”
皇帝发话了,臣子到底没站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结结巴巴道:“臣、臣——”
“起身吧。”赵嘉陵又说。她面上挂着淡笑,嗓音醇正平和,“祖先有灵,朕日夜思量不敢忘。只是天下安危系于朕一身,兹事体大,朕不可独断。诸卿至诚慷慨,是朕肱骨,宜协力同心才是。卿等可畅所欲言,无罪。”
朝臣竖着耳朵,试图从冠冕堂皇的套话中辨认出皇帝的真正心绪,可愣是没听着往日活泼的心思。
难道所言即所思?
不过话虽然是那样说的,但没谁敢真的放开来说道。
不治罪不代表着真的不处置啊,如果被圣人记恨了,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熬够了资历也爬不上去。
天书中罗列的纲目颇为新异,什么工学、化学看不大懂,就不说了。至于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合为一科,这意思倒是明了,不就是日后入国子监不再限制家世么?贵族子孙当与庶民同列。这点许多人也是不愿意的,然而前不久才闯出大祸,也不好在这个时候说道。思来想去,保守派找到一个攻讦点——兵学!
是的,贡举改制时要建武庙、设武监,至今仍有人心中愤愤不平。
趁此“畅所欲言”的机会,将兵学拉出来鞭挞,反正武臣们口舌颇为笨拙,廷上争事,最为无能。
不过……武臣们不会动手打人吧?文臣们视线悄悄地往禁卫身上扫一圈,天子仪仗在,来得及将他们从凶暴中解救出来,况且,这也能成为武臣不堪用的理由呢。
保守派臣子:“太平盛世当以仁义为先,臣以为当效法尧舜事,休兵止戈。只要将天下之贤才举为己用,奸邪谗慝之辈除去,四海自然无虞,而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自来宾贡。风俗敦厚,四方来归,又何须用武功?”①
武臣:“?”非得将他们挑出来当软柿子捏?
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愤怒地瞪着挑事的人,而那说话的臣子仍旧觉得不够,肥了胆子,朝着武臣——尤其是暴脾气的淮海侯露出一抹挑衅的神色。
淮海侯烦躁,但没动静。
昨日谢府悄悄遣人传讯,要他不必在意文臣议论,不可在朝堂动手。
一旦动手,兵学和武举就是活靶子,文臣们非得将它骂没了不可。既然兵学可撤,那其余不喜欢的科目呢?
谢兰藻深知文臣手段。
六部尚书中,工部存在感低微。不过此刻他站了出来,一叉手,清了清嗓道:“君子德风,小人德草。风行教化,正是职责。臣以为,当遣圣人徒往四海传圣人之教,使得海内外宾服。”
文臣:“?”
谁想到蛮夷之地去传圣人之教啊!工部尚书到底是哪边的?平日喝酒时候还埋怨武臣嗓门大呢,怎么现在替武人说话了?
工部尚书假装没看到同僚如利针般的视线。
望远之镜在手,谁不心血沸腾啊?甚至想要拿着望远镜往那瞭望塔一站,将四方鬼祟都映入眼中。
天降神物于大雍啊!
《课改指南》同样是诸帝所赐,还能是坏东西吗?
没法接的话茬就不接,偃旗息鼓的保守派退下,换得另一人上场,开口便是:“尧舜宰乾坤,器农不器兵。”②
“那设立农学,诸位总不会有异议吧?”司农卿幽幽地开口。
保守派才起了个调,就被司农卿打断了。眉头一皱,当即反驳道:“农人识农事,乃经验使然,何须建学?士农工商,各守其位,如何能让农夫与学生同列?”
![拯救偏执反派boss[快穿]](/img/28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