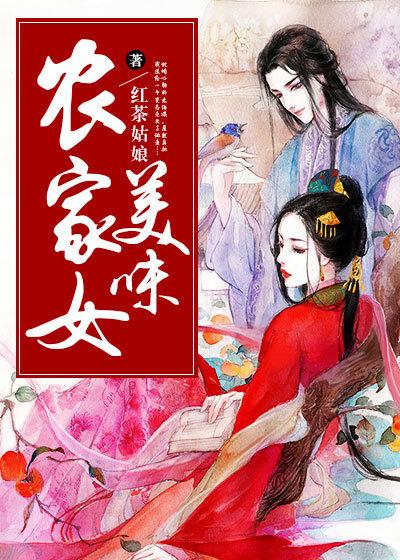笔趣阁>沧浪台 > 4550(第13页)
4550(第13页)
下一刻,乌衡干脆转守为攻,突然出手按住时亭肩膀,腾身翻起调换了两人位置。
时亭有点懵地躺在乌衡身下,意外地看着乌衡,恍然明白了什么,反讽道:“二殿下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不是病骨难支,柔弱不堪吗?”
乌衡装作没听到,定定看着时亭淡漠的双眼,贪婪地想要从里面窥探到别的情绪。
比如,面对他情动时的别样反应,或是别扭,或是厌恶,或是难堪,什么都好,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冷静理智到极致。
这时,房门从外面打开。
乌衡几乎是刹那扯开时亭半边衣衫,时亭第一反应是一脚将他踹开,但还是及时克制住,配合地抬手环住他脖子,暧昧地交缠在一起。
江奉的声音从床帘外传来:“我说了,你来的不是时候,急什么?”
“我不是说过,不能碰那位柳姑娘吗?”另一道声音响起,明显饱含怒火。
是徐世隆。
时亭顿时心思百转
——江奉用家人威胁并拉拢徐世隆后,竟然这么快让他参与雪罂这么重要的事宜中,是真的信任到了极致?还是宗亲和丁党并没那么水火不容,早就暗通款曲?
江奉瞥了眼床榻上的两道身影,轻嗤一声:“不过是个琴女,你至于就因为一曲《秋高》这么紧张吗?况且人家柳姑娘攀上乌衡这种高枝可乐意了。”
徐世隆道:“你不懂她们这种女子的无奈,不过也是为了生存罢了。”
江奉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不仅噗嗤笑出来:“你徐世隆竟然还能说出这般话来,你该不会忘记了是谁利用完宋锦又杀了她吧?”
徐世隆一噎,彻底没话说了。
时亭闻言不由意外。
他猜想过很多次宋锦背后的人是谁,但万万没有想到是徐世隆。他之前还愿意相信,当年这个为了给百姓申冤,不惜得罪宗亲士族的武状元还存有一份良心,纵然有丁道华的提携之恩,也不会沦为砍向无辜百姓的一把刀。
毕竟,抱春楼做的是雪罂的买卖,实打实的祸国殃民。
但物是人非才是人生百态。
乌衡一边假意做戏,趁机抬手抚上时亭眉眼,一边窥探其中情绪,难得寻觅到一丝掩不住的忧伤,不由跟着心里难受。
“柳姑娘,我轻点便是,别哭。”
乌衡轻轻唤了声,仰头凑近时亭,两人几乎脸贴着脸。
时亭只当是他又在做戏,没什么反应。
下一刻,乌衡将吻落在时亭的眼睛上,时亭根本来不及躲避,本能地眨了下眼睫,心底那点忧愁被瞬间一扫而空,惊讶地瞪向乌衡。
他之前只知道乌衡这人无奈,不曾想还会趁机当登徒子!
乌衡则是一副看不到时亭愤怒的模样,仗着现在两人得继续做戏,肆无忌惮地又吻了吻怀里人的眉心,然后将目光投向耳垂。
时亭的耳垂宛如白玉般,摸起来应该很软。
“二殿下。”
时亭低声警告,“我们不会在这待一辈子的。”
意思是惊鹤刀还没生锈,等自己出去,搞不好是要算总账的。
乌衡不禁笑了下,心想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才是上策,不是吗?
但就在乌衡色胆包天,想要亲手捏捏时亭耳垂时,床帘突然被拉开。紧接着,一件披风盖到时亭身上。
乌衡瞥了眼出手的徐世隆,知道和时亭的这场戏到此为止了,不由遗憾地捻了捻指尖的余温,顺着徐世隆推他的动作滚到一边,瘫着身子急促喘息,一副吸了雪罂神志不清的模样。
“柳姑娘,你没事吧?”徐世隆一把拉起时亭扶住,关心问道。
时亭见他满脸关心不像是假的,便装作弱不禁风的模样,撑着额头道:“我不知道,只觉得头晕眼花,浑身燥热。”
“柳姑娘放心,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徐世隆说着瞪了眼江奉,讽刺道,“只吸雪罂可没有燥热的效果,我看是有人故意放不干净的东西了。”
江奉也不甘示弱,嘲讽道:“宋锦生前不就是靠这些手段替你做事的吗,你不会都忘了吧?也对,你心底只会嫌她脏,不配进你徐家的门。”
“我杀她是因为她会坏丞相的事,坏我们的事。”徐世隆义正词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不是吗?”
江奉冷哼一声,道:“我本以为我已经够无耻了,没想到你比我还无耻,徐将军,以前我还真是小看你了。”